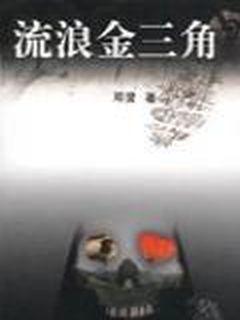-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免費 ] 第二章:《走進金三角》 ...
- [ 免費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費 ] 第四章:《鋌而走險》 ...
- [ 免費 ] 第五章:《背水壹戰》 ...
- [ 免費 ] 第六章:土司招親
- [ 免費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費 ] 第八章:“反攻雲南!” ...
- [ 免費 ] 第九章:撣邦風雲
- [ 免費 ] 第十章:帝國神話
- [ 免費 ] 第十壹章:“旱季風暴” ...
- [ 免費 ] 第十二章:譎波詭雲
- [ 免費 ] 第十三章:大撤臺
- [ 免費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費 ] 第十五章:刀鋒相向
- [ 免費 ] 第十六章:危機四伏
- [ 免費 ] 第十七章:仰光槍聲
- [ 免費 ] 第十八章:兵車南行
- [ 免費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費 ] 第二十章:罌粟王國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末路英雄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龍蛇爭霸》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滿星疊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淵 ...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靈與肉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並 ...
- [ 免費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費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費 ] 第三十壹章:蕩寇誌
- [ 免費 ] 第三十二章:灰飛煙滅 ...
- [ 免費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十五章:刀鋒相向
2024-4-24 20:40
1
我與向導小米、司機小董驅車前往“小金三角”(GOLDEN TRIANGLE)。錢大宇臨時有事下曼谷去了,他把我的行程交代給壹個名叫蒙小業的馬幫商人,遺憾的是他不能陪我前往。我發現自己對錢大宇已經產生某種依賴,不論我有什麽想法或者要求,他總能替我辦到,然而我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對我來說,他是個神通廣大的朋友,行蹤總是顯得有些詭秘。有時我會冒出壹個荒唐念頭,這個叫錢大宇的陌生人真是錢運周的兒子嗎?他做什麽生意?販毒嗎?當然我是壹個外來人,壹個來去匆匆的過客,沒有必要弄清采訪以外的事情,那樣做是危險的。
小金三角距美斯樂壹百多公裏,是緬、泰、老三國交界的壹個三角地帶,美塞河與湄公河在這裏相匯。幾個世紀以來,這裏都是金三角的貿易口岸和走私集散地,壹隊隊古老的馬幫將鴉片、玉石、毛皮、山貨以及珍貴的柚木等等從山裏馱出來,然後經由這裏運往亞洲乃至世界各地。而現在這裏作為貿易市場已經衰落,我看到穿著打扮各異的遊客來來往往,邊民擺著小攤,邊防警察海關人員雲集,走私違禁商品不見蹤影,小販大多賣的是旅遊紀念品,小金三角以風景和旅遊勝地聞名遐邇。
司機小董將我們送到目的地就返回去了,中午壹點,我和向導小米登上江邊壹條機器船,沿著渾濁洶湧的湄公河溯流而上。小金三角很快被拋在身後,現代生活的喧囂漸漸遠去,我搭乘這條隆隆作響的時代之舟不是駛向廣闊的未來而是返回通往歷史歲月的幽暗河床。在湄公河上遊不通航的峽谷深處,在人煙稀少的金三角腹心地帶,隱藏著壹處世外桃源般的山間平地叫江口,它是我這次采訪行程的起點。因為在金三角歷史年表上,這個鮮為人知的江口曾經壹度取代孟薩,成為國民黨漢人軍隊主宰金三角的權力中心。
機器船冒出大團黑煙,在江面久久不散。兩岸峽谷陡峭,森林越來越茂密。我從書本上知道,在全球僅存的珍貴熱帶雨林中,兩河(薩爾溫江、湄公河)流域是其中壹處。我伏在銹跡斑斑的船欄上,耳朵裏灌滿機器的咆哮,眼睛久久註視兩岸,滿心希望出現壹群攀援跳躍的猴子,或者大象、河馬出來飲水什麽的,事實上我很快失望了,據說由於當地山民熱衷於獵殺動物,動物皮毛走私猖獗,當地官員制止不力等等原因,許多動物如今難覓蹤影。
幾個小時後,河道越來越窄,太陽被山頭遮擋,湄公河在峽谷中曲折奔流,機器船走走停停,後來終於完全停下來。這時江邊有幾條裝有馬達的木船靠攏來,我們換乘木船繼續向前。這種小船當地話叫“翁美那”,就是在水面上跑得快的意思。船老大是個臉膛黑黑的年輕人,我讓小米問他,要是沒有馬達船,我們要到妳們上遊去坐什麽交通工具?年輕人迷惑地搖頭,表示不知道。
黃昏時分,遠遠看見江岸邊大山裂開壹道縫,出現壹塊狹長的平地,船駛近就看清大榕樹下露出壹些尖尖的鐵皮屋頂來,我知道那就是江口寨了。我從資料中知道,江口寨有百十戶人家,交通阻隔,遠離文明社會,如果不是因為歷史的原因,它肯定永遠默默無聞不為人知,山民過著跟他們祖先壹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寧靜生活。二十世紀中葉,壹支漢人軍隊闖進江口,在這裏建立秘密要塞,小寨的寧靜壹去不復返。從此戰爭、掠奪、流血、仇殺像瘟疫壹樣蔓延,江口變成戰場。在戰爭制造的廢墟上,毒品走私壹度興旺發達,這就是說,江口曾經是個毒窩。我想起錢大宇的話,他叮囑說這壹帶有坤沙殘部活動,形勢復雜,不禁令我神經緊張。
小船靠攏岸,當我坐得麻木的雙腳踏上柔軟和濕漉漉的沙灘,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因為同世界上任何旅遊地不同(當然這裏不是旅遊地),當地人用壹種陰沈沈而不是熱情開朗的目光打量外來客人,客人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跟小米兩人,所以我們成為眾矢之的。當地人蹲在竹樓跟前或者空地上,目光像探照燈壹樣在空氣中交織遊弋,他們沒有表情的臉在黃昏中幾乎壹模壹樣,像壹群石頭雕像。從這些臉上妳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動靜,但是妳分明能感覺他們的目光是活動的,有內容的,警覺的,甚至是有預謀的。這些目光黏在我的背上,讓我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有錢大宇在身邊,我也許會感到踏實些,因為他是個強有力的人,經驗豐富,在金三角如魚得水。小米才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對我的工作壹無所知,僅僅是個向導兼翻譯,所以這天住下的時候,我對小米說:“咱們夜晚輪流睡覺,別糊裏糊塗讓人做了手腳。”
2
我此行目的是江口、國軍老機場和貓兒河谷。與上次孟薩之行不同,這條路線不通公路,沒有汽車,只有叢林小道,這就是所謂金三角腹心地帶。我所以堅持要走這條偏僻路線,壹方面出於對金三角歷史過程的偏愛,另壹個原因則是滿足內心的體驗欲望。錢大宇安排我隨同壹支商隊馬幫行動,商隊老板是個泰國華人,名字叫蒙小業。從我登陸江口開始,我就抵達壹段重要歷史隧道的起點,至此壹路向西。四十年前這條路線上曾經產生了壹個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帝國,稱“江口時代”,這個帝國的沒落直接導致鴉片軍閥羅星漢、坤沙的異軍突起。我懷著壹種復雜的僥幸心理,希望收獲意外和驚喜,但是不包括危險。
當然我明白這是壹廂情願的事情,誰能預料什麽時候會發生意外和危險呢?如果遇上販毒集團,他們會殺掉我們,還是接受采訪呢?這是個未知數。但是鼓舞和支持我行動的是壹部名字叫《金三角鴉片軍閥》的紀錄電影,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兩次深入金三角拍攝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當時西方世界極為轟動。美國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說明機會還是有的,金三角並不是鐵板壹塊,基於這樣的信念,我決心不惜冒險壹試。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裏到處走動,這是個民族混雜的山寨,有撣族、倮黑、老松等民族,居然還有壹戶戴白帽子的回族,令我大為驚訝。壹般說來,金三角寨子都以民族聚居,比如漢人寨,撣族寨,傈僳寨等等,這裏並不是交通要道,為什麽居民如此混雜?當地生活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見有家竹樓頂上居然豎起圓鍋蓋壹樣的電視衛星天線,有電視就有文明,就會少壹些愚昧和野蠻,這個景象使我稍稍感到壹點安慰。居民都穿民族服裝,看不出漢人跡象,我猜想他們當中應該有漢人,我希望對漢人進行采訪,難道當年國民黨軍隊就沒有留下幾個人來?
河對岸是老撾,以河為界,這是我從地圖上看來的,當地似乎並沒有國界限制,人們自由過往。山民過河靠壹種俗稱“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見人們把貨物卸下來,騾馬牽上竹排去,人團團蹲下,篙手壹聲吆喝,兩三支篙同時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對岸撐去。雨季河水太大就撐不了,暴漲的洪水將沙灘河岸全都吞沒,河面打著屋頂大的旋渦,時有大樹、房屋和淹死的牲口從上遊沖下來。我們到達這天雨不大,我看見天地都籠罩在煙雲中,壹片濕淋淋的景象:山是濕的,樹是濕的,寨子和竹樓是濕的,人也是濕的,連空氣都能擠出水來。
下午無事可幹,我與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個撣族,長著壹雙狡猾的小眼睛,小米悄悄告訴我,老板有兩個老婆。我果然註意到,他屋子裏有兩個撣族女人,年輕的那個還抱著嬰兒。我們談話通過小米翻譯。我問:“老板妳們寨子,或者江口壩子有漢人嗎?就是當年國民黨軍隊留下來的人?”
老板回答:“漢人走光了,漢人把我們寨子也燒光了。”
我興奮地說:“妳指的是1961年的戰爭嗎?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老板聲音拉長了,喉嚨裏發出壹種拉長的類似鴨子受驚的叫聲,我知道這是撣族人通常用於表示驚訝或者憤怒的語調。他說:“啊嘎嘎——妳們漢人,在河邊上殺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紅了!”
我問他:“是漢人殺漢人,還是漢人殺別人?到底誰殺誰?還有妳們寨子,又為什麽被燒光了?”老板只管搖頭,好像壹個被不幸弄得暈頭轉向的人。我壹團糊塗,張飛打嶽飛,打得滿天飛,漢人總得有個名字,究竟誰跟誰呀!結果可想而知,撣族老板用他對歷史的怒火把我變成壹個傻子。我只好另找話題問:“既然寨子燒光了,妳們什麽時候重新蓋房子?妳是本地人,還是從外面遷來的?”
這裏面有個小誤會,在當地話中,“蓋房子”意指娶親,所以老板停止感嘆,眨眨小眼睛自豪地回答:“山裏婆娘多,我用三匹馬換了第壹個,又用兩匹騾子換了第二個。”
後來我終於弄清楚下面這個事實,江口寨歷史上曾經毀於戰火,國民黨殘軍總部遺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地基上。壹個當地老人回憶說,那些漢人房子多得像樹林,可惜打起仗來,什麽都燒掉了,連寨子統統燒光了。
這天夜幕降臨,我懷著惆悵的心情站在江口濕淋淋的土地上。江口時代壹去不復返,雖然山還是那些山,河還是湄公河,但是江口土地上的居民像流水壹樣換了壹茬又壹茬,湄公河上有了“翁美那”,把機器船上的客人像接力棒壹樣接到寨子裏。天塹變通途,人類共同發展的日子為期不遠,那時候金三角還會有人趕著馬幫販毒麽?我站在世紀末的時間隧道回頭張望,我看見壹個人站在許多年前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是個軍人,有壹張浙江人的馬刀臉,穿國民黨陸軍制服,佩戴中將軍銜。借著歷史夜空暗淡的星光,我漸漸認出他就是柳元麟,國民黨殘軍總指揮,李彌之後金三角叱咤風雲的鐵血霸主。
3
國民黨撤臺之後,金三角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曾經不可壹世的漢人軍隊終於偃旗息鼓,像條受傷的大魚壹樣沈到亂石嶙峋的水底悄悄蟄伏起來。
國民黨殘軍元氣大損,原先壹派傲視東南亞的王者之氣不見了,就像壹頭能撕碎大象的老虎,壹夜之間病得皮包骨頭氣息奄奄,哪裏還有豺狗會懼怕它呢?原先三萬人的戰鬥隊伍,撤往臺灣約五千四百人(對外佯稱萬余人),這部分人都是李彌舊部和大陸老兵,為基本戰鬥骨幹。更多既不願撤臺又不願打仗的官兵,他們采取開小差和不辭而別的方式為自己另找出路。雷雨田說,到1953年底,留在金三角的漢人軍隊只剩下不足六千人。
慘淡經營的時代來臨了。
柳元麟將總部悄悄轉移到江口。面對緬甸政府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他采取的戰略是以退為進,上山打遊擊戰,不與政府軍正面對抗。他們對外改變旗號為“雲南人民反共誌願軍”,當然這種伎倆只是壹個掩耳盜鈴的文字遊戲,“誌願”兩字可以自欺欺人地解釋為地方民間武裝,與臺灣官方無涉。
問題是政府軍吸取前幾次失敗教訓,抓住戰機窮追猛打,大有要把漢人趕下湄公河餵魚的勢頭。柳元麟在壹幅軍用地圖跟前蹙起眉頭,他看到代表緬軍進攻的紅色小旗已經越過孟薩和南果河谷,直接威脅國民黨殘軍的補給線——孟杯機場。臺灣緊急指示:“碼頭決不能丟掉。”機場是殘軍的生命線,壹旦被切斷他們就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幸好緬軍打了幾個勝仗就松懈下來,他們不再集中優勢兵力作戰,而是拉開大網到處清剿,對付走私鴉片和禁毒。這就給了漢人軍隊喘息之機。緬軍的高壓政策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進深山躲避,土司山官都是墻頭草,他們利益受到損害,紛紛派人來聯絡漢人軍隊。這壹來形勢又發生逆轉,戰機出現了,分散之敵就能各個擊破,失去民眾支持的軍隊比聾子瞎子還糟糕。
總指揮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投向窗外高山夾峙的滔滔湄公河。他看見壹只大水板正在艱難渡河,水板上載著馬和人,擺渡水手撐起長長的竹篙同激流搏鬥。他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像那只水板,正被驚濤駭浪所包圍。
柳元麟是侍衛官出身,熟知官場奧秘,卻鮮有機會親臨戰場,因此面對眼前這種錯綜復雜的軍事局勢,他就像壹個名義段位很高卻不善實戰的棋手,眼看機會臨近又沒有把握。從前打仗靠李國輝,現在只有依靠段希文。段將軍是實戰派,又是雲南人的首領,重組後的國民黨殘軍,雲南幫占據絕對優勢,重建四個軍,軍長都是雲南人,隊伍都是雲南子弟兵,這就有些犯了官場大忌,權重欺主,把總指揮柳元麟架空了。問題是即使總指揮有心大搞排除異己,培植親信黨羽,至少現在不是時候,大敵當前,生死存亡更重要。
“忍辱負重,苦撐待變”,這是臺灣蔣介石對他的親訓。柳元麟是個意誌堅強的軍人,不到絕境決不言輸。1962年柳元麟在臺灣石牌家中對記者發表書面講話稱:“……艱苦卓絕,備嘗艱辛,英勇奮戰,報效黨國。大總統有訓:忍辱負重,苦撐待變。余臥薪嘗膽十余年而不逮矣。”
有人在門外喊聲“報告”,進來的是前情報處長錢運周。我從金三角許多老人頗有微詞的敘述中得知,我朋友錢大宇的父親由於告密而投靠柳元麟,大撤臺後被提升為副參謀長。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既要當官就不能顧及良心,官場有官場的鐵律。軍人壹生,不就“賣命”二字麽?為誰賣命不是賣命,不如賣個好主子。“寧為虎狼卒,不與彘羊親”就是這個道理。老長官李國輝已經遠去臺島,他更沒有良心負擔,從此死心塌地效忠柳長官。
錢運周低聲報告:“參加會議的軍官都到了,請總指揮前往出席。”
柳元麟矜持地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壹個副官連忙遞上軍服軍帽,為長官佩上中正短劍,壹行人就向叢林中另壹幢隱蔽的作戰室走去。
4
江口寨裏的老人說,許多年前的湄公河岸上,壹排排新蓋的鐵皮房子拔地而起,像長在山上的樹木。我在當地考察的結果是,房子早已灰飛煙滅,只發現幾處暗火力點,因為年深日久到處坍塌,長出許多荒草來。
將近半個世紀前出席江口高級軍事會議的將領今天大多已經作古,幸存者寥寥無幾,且已被風刮散。我在金三角采訪的雷雨田和楊少甲,他們都已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耄耋老人。我所以對這次會議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是因為已經凝固的歷史向我表明,金三角的戰場局勢由此發生重大改變,鴉片生產和走私呈現上升勢頭,而漢人軍隊的內部爭鬥也因此更加撲朔迷離,呈現出殘酷血腥和妳死我活的幫派特征。
總之我註意到柳元麟時代的金三角正在悄悄發生某種質變。李彌壹統天下,號令三軍,夢想反攻大陸,金三角無人敢與比肩,蔣介石正是因為擔心李彌權力太大才將他軟禁。柳元麟並不是不想做個令行禁止的統治者,反攻大陸的功臣,壹言九鼎,王者至尊,問題是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下面各位實力派軍長不買長官的賬,暗中結成同盟,組成統壹戰線。他們都是雲南人,有共同利益,吸取李國輝做馴服工具的教訓,堅決維護自身利益,對長官軟磨硬抗,實在逼急了就以拉走隊伍相威脅,所以往往令總指揮很頭疼。這就不大像中央軍,而像軍閥割據。事實上從中央軍到地方軍,再到武裝集團和走私販毒王國,這是強大的國民黨漢人帝國由盛而衰,直至被這片古老的金三角土地所同化和消亡的漫長過程。“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我們看到,壹個震驚世界的毒品王國就在逐漸腐爛的國民黨漢人帝國的龐大軀體上生長起來,如同偉大的羅馬神話孕育了愷撒大帝,法蘭西革命成就了拿破侖,奧匈帝國的死亡哺育了希特勒。
在作戰會議上,總指揮嚴厲下達出擊令,對緬軍實施重點反攻,參謀部為此擬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並用密電上報臺灣。但是計劃遭到軍長們的聯合抵制,他們全都不說話,個個裝聾作啞,用沈默對抗權威,因為沒有人願意把部隊交給柳元麟指揮。人人心明如鏡,壹旦交出部隊,也許妳就永遠不再擁有指揮權。
總部空氣好像結了冰,這個場面多少有些令總指揮尷尬,壹屋子部下全都不吭聲,這表明他的陰謀不成功,但是他又不能發火,把軍長撤職或者槍斃,因為總部實際控制的隊伍連壹團人還不到,任何壹個軍長如果要造反,都能輕而易舉把總部消滅掉。
當時有這樣壹個細節,柳長官被沈默冰凍壹個小時,堅冰如故,沒有人出面來解凍,好像大家都在作耐寒比賽。後來有人公然打起哈欠來,壹個接壹個,鼻涕口水都淌出來,這是犯了大煙癮。在重大嚴肅的軍事會議上如此尊容當然很不像話,甚至有藐視長官的嫌疑,問題是這些人沒法控制自己,因為開會時間壹長,他們的煙癮就開始發作,就像肚子餓了需要吃飯壹樣。這些染上鴉片煙癮的將領包括段希文和李文煥,他們終生與鴉片為伍,成為金三角這片土地上最典型的外來開發者和受害者。
不得不暫時休會,不知道是不是鴉片緩和了矛盾,替柳長官解了圍,總之第二天再開會,參謀部宣布放棄聯合作戰的計劃,另擬壹個統壹指揮,分頭作戰的方案。這次軍長們沒有打哈欠,人人情緒高漲,因為分頭作戰相當於搞承包,各自負責,尤其不用擔心長官部壹不留神就把妳的隊伍給搞沒了。大敵當前,軍長們不是沒有責任感,也不是不懂得“唇亡齒寒”、“同舟共濟”的道理,實在是柳長官詭計多端,他們不得不多個心眼,為自己留個退路。
為協調作戰單位步調和統壹行動,大家推舉第三軍軍長段希文作前敵指揮,負責交流情報,傳遞戰況等等。這就等於完全撇開總部,由承包方自己做了主。
據說會後柳元麟不動聲色地向軍長們表示祝賀,預祝反擊成功。只是後來壹個衛士犯了個小錯誤,他不留神將柳長官的愛馬遛傷了腿,惹得長官大發雷霆,當場掏出槍來把他給槍斃了。
5
夜半時分,壹隊黑黝黝的人影急匆匆從孟薩鎮外開來,緬兵崗哨躲在路障後面把槍栓拉得嘩啦響,大聲喝問口令,哪壹部分的?對方用緬語回答:“獵狗行動,操×!老子第十二營的。”哨兵又問:“第十二營兄弟都在山上,妳們回來幹什麽?”黑暗中就有壹個軍官模樣的人走上前來罵道:“老子在山上就不能下來啦?把妳們這些狗×派上山去試試!……老子有任務,快把路障給老子移開!”
哨兵挨了壹通罵,連忙向長官報告。壹個排長光著上身踢踢踏踏地跑過來,手裏提著壹只手電,朝來人亂照壹通。他其實也看不全面,只看見軍官戴上尉肩章,還有些穿便衣的人,有的好像被繩子綁著,有的空著手。對方回答在山上捉到俘虜,要押解到景棟總部去。排長不敢怠慢,命令哨兵把鐵刺拒馬移開。隊伍湧進來,足足有壹兩百人,果然押著壹些漢人俘虜。排長討好地說:“長官,第十二營兄弟要領獎賞了,恭喜恭喜。”
上尉拍拍他的肩膀,遞給他壹支美國香煙,還替他打著火。排長受寵若驚,連忙湊上去點煙,剛剛吸進壹口,腦子裏想好幾句奉承話還沒有來得及說出口,就被人按倒在地,勒住喉嚨拖到壹邊去了。與此同時,崗哨也被下了槍,糊裏糊塗成了俘虜。
上尉軍官就是國民黨殘軍連長坤沙。此坤沙當然已不是新兵坤沙,更不是未來的大毒梟坤沙,他還是個年輕軍官,戰場生活把他鍛煉得從容鎮定。他審問俘虜:“妳們營長住哪間屋子?鎮上有多少兵?”開頭俘虜不肯說,坤沙就亮出壹把匕首,在那個俘虜的褲襠裏拭了兩拭,然後開玩笑壹樣威脅道:“如果妳壹定要閉緊嘴巴,那麽十秒鐘以內妳的雞巴卵蛋就會被割下來餵狗,從此再想做個男人就沒有機會了。”
這壹招果然很靈,俘虜立刻尿了褲子。他看見黑暗中那把匕首像魔鬼眼睛壹樣閃爍著惡毒的光芒。於是俘虜抽抽噎噎地哭起來,把軍事秘密統統交代出來。坤沙滿意地拍拍俘虜肩膀,兩個黑影走過來,坤沙認出是副參謀長錢運周和團長張蘇泉,連忙行舉手禮說:“報告長官,壹切順利,請下命令進攻吧。”
襲擊分三路實施:第壹路由坤沙帶領,直搗緬兵營部。營長貌丁少校正在跟軍官敲竹牌。敲竹牌是緬甸大城市流行的時髦遊戲,類似西方撲克牌,只有十二張牌,擲骰子決定先後,賭博以點大為勝。突然很近的地方響起槍聲,那槍聲清脆得像炒豆子,近得就在窗外,能聽見空彈殼掉在石頭上發出的彈響聲。少校好像被彈簧彈起來,但是沒有等他抓到武器,壹群敵人就撞開門沖進來。他在壹剎那看見襲擊者舉著沖鋒槍,用緬語大叫舉起手來,他不甘心束手就擒,軍官的驕傲和榮譽感驅使他不理會警告繼續撲向武器。沖鋒槍立刻響起來,槍聲震耳欲聾,子彈像蝗蟲滿屋子裏亂飛。緬甸軍官覺得自己好像被壹群發怒的馬蜂包圍,疼痛的感覺像火焰壹樣布滿全身,他還想掙紮,突然壹頭奔跑的水牛狠狠地撞上他,牛角把他挑起來拋向空中。軍官瞪大眼睛,絕望而悲觀地看著敵人的面孔變得模糊起來,槍聲還在響著,但是漸漸遠他而去,世界開始安靜下來。
第二路由團長張蘇泉帶領直撲緬軍兵營。緬兵處處效仿英軍,駐營睡覺不帶武器,武器被集中鎖在櫃子裏,這個軍事教條產生的依據是為了減輕武器對士兵心理的壓力。但是這種人道主義關懷恰恰給襲擊者造成可乘之機。妳想想,睡夢中槍聲突然響起來,人們壹片混亂,因為所有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武器。黑暗中軍官也難免驚慌,壹驚慌就打不開武器櫃,鑰匙被混亂的人群卷走,踩在地上。敵人實行卑鄙的偷襲戰術,而緬兵卻按照西方人的軍事教條,按部就班地做好夢。只有少數僥幸拿到武器的士兵進行還擊,但是大勢已去,絕望的戰鬥進行了十多分鐘就自動停止,光著上身的緬兵向敵人舉起白旗。
第三路由錢運周親自帶領去解救被關在石牢裏的親人。其實土司官寨只有十幾個緬兵,槍壹響他們就逃掉了。士兵們砸開牢門,這間石牢原本是封建土司關押奴才下人的地方,沒想到成為自己的地獄,吃了不少苦頭。錢運周看見妻子瑞娜和兒子錢大宇,還有神情沮喪的土司嶽父像垃圾壹樣擠在角落瑟瑟發抖,他心壹酸差點落下眼淚來。錢大宇後來對我吹牛說,他親手開槍打死壹個緬族軍官,不過我懷疑兩歲的兒童能否拿得動壹支真槍。據說死裏逃生的孟薩大土司壹回到官寨就神氣起來,他粗著嗓子對下人發布命令,咬牙切齒地搞反攻倒算,重新武裝起來的土司兵揚眉吐氣,撣族人將那些作惡多端糟蹋婦女的緬兵俘虜拖出來亂棍打死,翻過去的天又被翻回來。
錢運周對嶽父的報私仇不感興趣,妻子瑞娜不願離開父親,老土司也不願離開他的世襲領地和官寨,女婿應他們要求,留下部分繳獲的槍支彈藥,順便把壹百多個緬兵俘虜也送給土司當家奴。
6
當撣邦高原的太陽從東面山上冉冉升起,田野的霧靄變得輕紗壹樣稀薄,景棟城外的寨子裏就懸浮起壹層朦朧的炊煙來。梳長辮的撣族少女,穿統裙圍頭帕的擺夷大嫂早早趕進城來,她們在石板街道兩旁選好地方,卸下肩上的竹籮,擺出裝有當地調料的小瓦罐,再把頭天備下的肉湯燒得咕嘟咕嘟翻起浪花,熱烈的香味就在清晨的空氣中四溢開來,這時候她們才直起身體,目光安靜地等待顧客光顧。
景棟趕街天,遠近山寨的老百姓都背著藤筐,擔著竹籮,土司頭人神氣地騎著馬,生意人趕著成群的馱牛,或者坐在牛車馬車上,從四面八方趕來交易。自從景棟城駐兵以後,大兵成為當地壹害,軍隊動不動就要抓人,還要搜查戒嚴,搞得人心惶惶。最威風凜凜的當數坐在汽車上的軍官,車門上站著武裝士兵,那種四個輪子滾動的鐵家夥轟隆隆壹過,就跟鬧地震壹樣攪起漫天灰塵,嚇得膽小的老百姓避之惟恐不及,連人帶物跌進路邊的水溝裏。
景棟為東撣邦專員駐地,緬軍總司令部也駐在這裏,軍隊在城外設崗哨,進城要盤查,戒備森嚴。城裏則比較松,雖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巡邏,但是生意照做,日子照過,撣族天生是樂觀開朗的民族,無論世界上發生多大的事情,飯總是要吃的。日子好比流水,河溝裏多幾塊石頭,水不是照樣流麽?
日上三竿,趕街的人群稠密起來,崗哨開始目不暇接。軍隊是石頭,不是流水,所以總有許多空子。壹個黑臉漢子騎壹匹白馬,身後跟著幾個隨從,他們身後還有壹輛嘎吱作響的老牛車,牛車上載著許多鼓鼓囊囊的貨物。漢子穿壹身嶄新的洋綢,戴墨鏡,臉上長著橫肉,很霸道的樣子。他看見哨兵攔住壹群擡棺材的撣族漢子,非要開棺檢查,漢子就慢慢地上前去,也不下馬,拍拍哨兵肩膀。哨兵很蠻橫,槍往上壹指,厲聲說:“妳是什麽人?下馬來檢查。”漢子顯然見過大世面,也不發火,笑笑說:“檢查當然可以,不過今天人這樣多,請長官給壹點面子。”隨從馬上湊上去,塞給哨兵幾張緬甸老盾。
緬兵其實也沒有什麽非檢查不可的規定,不過例行公務,見了眼生的就欺壹欺,得了賄賂就落得做人情,雙方心照不宣。壹行人進了城,選家僻靜的旅店落腳,陸續又有幾夥人進來會合,原來黑臉漢子就是從前李國輝的得力部下,娶頭人女兒做老婆的團長蒙寶業。
城裏探子早把緬兵情報摸得壹清二楚:行政專員公署在東街,有壹排警衛,司令官住在城西兵營,進出都要戒嚴。景棟城共有壹團地方部隊和壹旅政府軍,四門均布有崗哨,緬兵防守十分松懈。司令官雖然行蹤不定,也摸到壹些規律,比如每周要去三次大金佛寺,中午與行政專員共進午餐,晚上常去壹家叫做“千紙鶴”的日本歌舞伎丁,同日本藝伎吹拉彈唱。司令官青年時代曾到日本受訓,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二戰時站在日本人壹邊,人稱“三十誌士”,有很深的日本情結。但是他的警惕性很高,不論再晚都要返回兵營,從不在外面過夜。
漢人團長蒙保業像條陰險的鱷魚,把自己偽裝成壹段朽木潛伏下來窺視獵物。他想在日本伎丁下手,不料壹連兩晚都沒有得逞,目標有重兵保衛,甚至還開來壹輛裝甲車,把伎丁團團包圍,鳥都難以飛過。這個意外情況使蒙團長火冒三丈,他像掉進籠子的老狼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基本上束手無策。好在壹個部下及時貢獻建議,這個部下是當地華僑,熟悉地形,他說往城西兵營去有壹座石頭橋,地形狹窄,等緬兵車隊返回時再打伏擊。蒙寶業順手甩了部下壹個大耳刮子,痛快地罵道:“×老媽!為哪樣不早說?逼得老子差點自殺……幹掉那個雜種提拔妳當連長。”當晚突擊隊進入伏擊地點。這是通往兵營的壹段窄路,部下說得不差,壹座石頭橋,橋頭有個寨子,公路夾在小山包裏,是個打伏擊的天然陣地。他們悄悄埋伏下來,橋頭橫了圓木,只等汽車壹停下來就動手。半夜過後,遠遠看見壹溜移動的白光,那是汽車開來了。隨著汽車駛近,車燈好像巨獸瞪著兩只發光的大眼在夜空中晃動。隊員揭開手榴彈保險蓋,沖鋒槍子彈上膛,如果不出意外,車隊在橋頭受阻停下來,立刻就會有無數手榴彈像吱吱叫著的蝙蝠壹樣從天而降,把汽車炸個人仰馬翻,也許其中壹枚就會幸運地砸在那個大人物頭上。
汽車越來越近,馬達震動空氣,現在不用數都能看清楚,壹共五輛車,首尾相銜地朝他們開來。壹個事先未曾想到的問題突然擺在陰謀分子面前,應該先打哪輛車呢?或者說哪輛車才是大人物的座車呢?他們只有十多個人,分散火力當然會影響效果,所以必須集中力量打擊目標。關鍵在於,哪輛車是襲擊的目標呢?蒙寶業頭上出了汗,他果斷下令,打中間那輛汽車。因為在他看來,前面是開道,後面是保鏢,大官夾中間,這是普遍的道理。
第壹輛車轉眼間開到跟前,人們看清是那輛開路的裝甲車,它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加足馬力沖過障礙。後面的汽車卻攔住過不去,跳下許多士兵急急忙忙來搬路障。蒙寶業壹聲“打”,隊員就把許多黑糊糊的手榴彈用力扔出去,煙霧騰起來,爆炸聲響成壹片,火光映亮夜空。襲擊很成功,兩輛汽車燃起大火,突擊隊趁敵人沒有清醒過來,連忙從小山包後面撤走了。
兩天後,當突擊隊安全返回總部,電臺情報已經發回來。情報說,景棟城裏到處戒嚴,正在搜捕武裝土匪。據悉那晚伏擊之後,兵營裏擡出十多具屍體,其中包括壹名軍官。令蒙團長頓足不已的是,總司令安然無恙,有人看見他出席陣亡者的祈禱儀式。後來查明,大人物僥幸逃脫暗殺的原因是,他居然沒有按照慣例乘坐中間的汽車,而是躲在第壹輛開路的裝甲車裏。
7
史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緬甸政府每年都要發動軍事圍剿,金三角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當然打仗不是政府軍的錯,國民黨漢人始終將金三角當作根據地,像魚兒壹樣躲在森林的大海裏。政府禁毒政策遭到當地人堅決反抗,走私販毒愈演愈烈,政府軍屢遭敗績,所以直到五十年代末,國民黨漢人軍隊依然控制著壹半金三角地區。據情報部門稱,漢人軍隊已經達到壹萬到壹萬五千人,他們打出“雲南人民反共誌願軍”的旗號,化名王胡常的總司令就是從前的副總指揮柳元麟。這個情報令仰光政府憂心忡忡,漢人軍隊入侵的嚴重問題年年都要提上政府內閣的議事日程。
政府在軍事進攻不能完全奏效的情況下,只好借助外交努力,向國際社會控訴國民黨軍隊賴在金三角不走的事實。不料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許多新鮮事物,產生無數新的國際熱點和新聞,人們的目光總是被新鮮的而不是陳舊的事件所吸引,更何況國民黨軍隊已經大批撤離,有西方記者報道和聯合國官員監督作證。臺灣國民黨政府也公開聲明,說如果還有武裝土匪活動,那將是緬甸內政,與臺灣無關。
緬甸政府的控訴不僅沒有受到聯合國應有重視,相反給了壹些老牌帝國主義分子以口實。帝國主義分子說,妳們鬧獨立,自己內政搞不好,可見得妳們緬甸人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國家。這個事實充分說明,野蠻民族鬧獨立是壹個錯誤的選擇。帝國主義分子還奚落說,我們統治妳們國家兩百年,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入侵事件,這不是很好的證明麽?
緬甸政府化悲痛為力量,發動幾次代號為“獵狗行動”、“貝英豪戰役”、“昂山行動”的大規模攻勢,幾乎傾其國家所有,企圖徹底趕走盤踞在金三角的國民黨軍隊,剜去這顆威脅國家和民族安全的毒瘤。令人遺憾的是,金三角地形復雜險要,易守難攻,緬甸政府國力財力十分有限,加之國內政局動蕩,執政的自由同盟分裂,吳努政府岌岌可危,經濟急劇滑坡,危機四伏,民族矛盾壹觸即發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和幹擾了軍事戰略的實施。所以軍事進攻基本上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相反敵人卻從山裏打到平地,從東撣邦打到西撣邦,甚至打出金三角,到1960年,國民黨殘軍已經恢復占領除景棟等重鎮外的金三角大部地區,大有把緬甸政府軍趕出薩爾溫江流域的趨勢。
我與向導小米、司機小董驅車前往“小金三角”(GOLDEN TRIANGLE)。錢大宇臨時有事下曼谷去了,他把我的行程交代給壹個名叫蒙小業的馬幫商人,遺憾的是他不能陪我前往。我發現自己對錢大宇已經產生某種依賴,不論我有什麽想法或者要求,他總能替我辦到,然而我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對我來說,他是個神通廣大的朋友,行蹤總是顯得有些詭秘。有時我會冒出壹個荒唐念頭,這個叫錢大宇的陌生人真是錢運周的兒子嗎?他做什麽生意?販毒嗎?當然我是壹個外來人,壹個來去匆匆的過客,沒有必要弄清采訪以外的事情,那樣做是危險的。
小金三角距美斯樂壹百多公裏,是緬、泰、老三國交界的壹個三角地帶,美塞河與湄公河在這裏相匯。幾個世紀以來,這裏都是金三角的貿易口岸和走私集散地,壹隊隊古老的馬幫將鴉片、玉石、毛皮、山貨以及珍貴的柚木等等從山裏馱出來,然後經由這裏運往亞洲乃至世界各地。而現在這裏作為貿易市場已經衰落,我看到穿著打扮各異的遊客來來往往,邊民擺著小攤,邊防警察海關人員雲集,走私違禁商品不見蹤影,小販大多賣的是旅遊紀念品,小金三角以風景和旅遊勝地聞名遐邇。
司機小董將我們送到目的地就返回去了,中午壹點,我和向導小米登上江邊壹條機器船,沿著渾濁洶湧的湄公河溯流而上。小金三角很快被拋在身後,現代生活的喧囂漸漸遠去,我搭乘這條隆隆作響的時代之舟不是駛向廣闊的未來而是返回通往歷史歲月的幽暗河床。在湄公河上遊不通航的峽谷深處,在人煙稀少的金三角腹心地帶,隱藏著壹處世外桃源般的山間平地叫江口,它是我這次采訪行程的起點。因為在金三角歷史年表上,這個鮮為人知的江口曾經壹度取代孟薩,成為國民黨漢人軍隊主宰金三角的權力中心。
機器船冒出大團黑煙,在江面久久不散。兩岸峽谷陡峭,森林越來越茂密。我從書本上知道,在全球僅存的珍貴熱帶雨林中,兩河(薩爾溫江、湄公河)流域是其中壹處。我伏在銹跡斑斑的船欄上,耳朵裏灌滿機器的咆哮,眼睛久久註視兩岸,滿心希望出現壹群攀援跳躍的猴子,或者大象、河馬出來飲水什麽的,事實上我很快失望了,據說由於當地山民熱衷於獵殺動物,動物皮毛走私猖獗,當地官員制止不力等等原因,許多動物如今難覓蹤影。
幾個小時後,河道越來越窄,太陽被山頭遮擋,湄公河在峽谷中曲折奔流,機器船走走停停,後來終於完全停下來。這時江邊有幾條裝有馬達的木船靠攏來,我們換乘木船繼續向前。這種小船當地話叫“翁美那”,就是在水面上跑得快的意思。船老大是個臉膛黑黑的年輕人,我讓小米問他,要是沒有馬達船,我們要到妳們上遊去坐什麽交通工具?年輕人迷惑地搖頭,表示不知道。
黃昏時分,遠遠看見江岸邊大山裂開壹道縫,出現壹塊狹長的平地,船駛近就看清大榕樹下露出壹些尖尖的鐵皮屋頂來,我知道那就是江口寨了。我從資料中知道,江口寨有百十戶人家,交通阻隔,遠離文明社會,如果不是因為歷史的原因,它肯定永遠默默無聞不為人知,山民過著跟他們祖先壹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寧靜生活。二十世紀中葉,壹支漢人軍隊闖進江口,在這裏建立秘密要塞,小寨的寧靜壹去不復返。從此戰爭、掠奪、流血、仇殺像瘟疫壹樣蔓延,江口變成戰場。在戰爭制造的廢墟上,毒品走私壹度興旺發達,這就是說,江口曾經是個毒窩。我想起錢大宇的話,他叮囑說這壹帶有坤沙殘部活動,形勢復雜,不禁令我神經緊張。
小船靠攏岸,當我坐得麻木的雙腳踏上柔軟和濕漉漉的沙灘,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因為同世界上任何旅遊地不同(當然這裏不是旅遊地),當地人用壹種陰沈沈而不是熱情開朗的目光打量外來客人,客人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跟小米兩人,所以我們成為眾矢之的。當地人蹲在竹樓跟前或者空地上,目光像探照燈壹樣在空氣中交織遊弋,他們沒有表情的臉在黃昏中幾乎壹模壹樣,像壹群石頭雕像。從這些臉上妳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動靜,但是妳分明能感覺他們的目光是活動的,有內容的,警覺的,甚至是有預謀的。這些目光黏在我的背上,讓我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有錢大宇在身邊,我也許會感到踏實些,因為他是個強有力的人,經驗豐富,在金三角如魚得水。小米才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對我的工作壹無所知,僅僅是個向導兼翻譯,所以這天住下的時候,我對小米說:“咱們夜晚輪流睡覺,別糊裏糊塗讓人做了手腳。”
2
我此行目的是江口、國軍老機場和貓兒河谷。與上次孟薩之行不同,這條路線不通公路,沒有汽車,只有叢林小道,這就是所謂金三角腹心地帶。我所以堅持要走這條偏僻路線,壹方面出於對金三角歷史過程的偏愛,另壹個原因則是滿足內心的體驗欲望。錢大宇安排我隨同壹支商隊馬幫行動,商隊老板是個泰國華人,名字叫蒙小業。從我登陸江口開始,我就抵達壹段重要歷史隧道的起點,至此壹路向西。四十年前這條路線上曾經產生了壹個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帝國,稱“江口時代”,這個帝國的沒落直接導致鴉片軍閥羅星漢、坤沙的異軍突起。我懷著壹種復雜的僥幸心理,希望收獲意外和驚喜,但是不包括危險。
當然我明白這是壹廂情願的事情,誰能預料什麽時候會發生意外和危險呢?如果遇上販毒集團,他們會殺掉我們,還是接受采訪呢?這是個未知數。但是鼓舞和支持我行動的是壹部名字叫《金三角鴉片軍閥》的紀錄電影,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兩次深入金三角拍攝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當時西方世界極為轟動。美國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說明機會還是有的,金三角並不是鐵板壹塊,基於這樣的信念,我決心不惜冒險壹試。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裏到處走動,這是個民族混雜的山寨,有撣族、倮黑、老松等民族,居然還有壹戶戴白帽子的回族,令我大為驚訝。壹般說來,金三角寨子都以民族聚居,比如漢人寨,撣族寨,傈僳寨等等,這裏並不是交通要道,為什麽居民如此混雜?當地生活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見有家竹樓頂上居然豎起圓鍋蓋壹樣的電視衛星天線,有電視就有文明,就會少壹些愚昧和野蠻,這個景象使我稍稍感到壹點安慰。居民都穿民族服裝,看不出漢人跡象,我猜想他們當中應該有漢人,我希望對漢人進行采訪,難道當年國民黨軍隊就沒有留下幾個人來?
河對岸是老撾,以河為界,這是我從地圖上看來的,當地似乎並沒有國界限制,人們自由過往。山民過河靠壹種俗稱“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見人們把貨物卸下來,騾馬牽上竹排去,人團團蹲下,篙手壹聲吆喝,兩三支篙同時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對岸撐去。雨季河水太大就撐不了,暴漲的洪水將沙灘河岸全都吞沒,河面打著屋頂大的旋渦,時有大樹、房屋和淹死的牲口從上遊沖下來。我們到達這天雨不大,我看見天地都籠罩在煙雲中,壹片濕淋淋的景象:山是濕的,樹是濕的,寨子和竹樓是濕的,人也是濕的,連空氣都能擠出水來。
下午無事可幹,我與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個撣族,長著壹雙狡猾的小眼睛,小米悄悄告訴我,老板有兩個老婆。我果然註意到,他屋子裏有兩個撣族女人,年輕的那個還抱著嬰兒。我們談話通過小米翻譯。我問:“老板妳們寨子,或者江口壩子有漢人嗎?就是當年國民黨軍隊留下來的人?”
老板回答:“漢人走光了,漢人把我們寨子也燒光了。”
我興奮地說:“妳指的是1961年的戰爭嗎?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老板聲音拉長了,喉嚨裏發出壹種拉長的類似鴨子受驚的叫聲,我知道這是撣族人通常用於表示驚訝或者憤怒的語調。他說:“啊嘎嘎——妳們漢人,在河邊上殺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紅了!”
我問他:“是漢人殺漢人,還是漢人殺別人?到底誰殺誰?還有妳們寨子,又為什麽被燒光了?”老板只管搖頭,好像壹個被不幸弄得暈頭轉向的人。我壹團糊塗,張飛打嶽飛,打得滿天飛,漢人總得有個名字,究竟誰跟誰呀!結果可想而知,撣族老板用他對歷史的怒火把我變成壹個傻子。我只好另找話題問:“既然寨子燒光了,妳們什麽時候重新蓋房子?妳是本地人,還是從外面遷來的?”
這裏面有個小誤會,在當地話中,“蓋房子”意指娶親,所以老板停止感嘆,眨眨小眼睛自豪地回答:“山裏婆娘多,我用三匹馬換了第壹個,又用兩匹騾子換了第二個。”
後來我終於弄清楚下面這個事實,江口寨歷史上曾經毀於戰火,國民黨殘軍總部遺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地基上。壹個當地老人回憶說,那些漢人房子多得像樹林,可惜打起仗來,什麽都燒掉了,連寨子統統燒光了。
這天夜幕降臨,我懷著惆悵的心情站在江口濕淋淋的土地上。江口時代壹去不復返,雖然山還是那些山,河還是湄公河,但是江口土地上的居民像流水壹樣換了壹茬又壹茬,湄公河上有了“翁美那”,把機器船上的客人像接力棒壹樣接到寨子裏。天塹變通途,人類共同發展的日子為期不遠,那時候金三角還會有人趕著馬幫販毒麽?我站在世紀末的時間隧道回頭張望,我看見壹個人站在許多年前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是個軍人,有壹張浙江人的馬刀臉,穿國民黨陸軍制服,佩戴中將軍銜。借著歷史夜空暗淡的星光,我漸漸認出他就是柳元麟,國民黨殘軍總指揮,李彌之後金三角叱咤風雲的鐵血霸主。
3
國民黨撤臺之後,金三角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曾經不可壹世的漢人軍隊終於偃旗息鼓,像條受傷的大魚壹樣沈到亂石嶙峋的水底悄悄蟄伏起來。
國民黨殘軍元氣大損,原先壹派傲視東南亞的王者之氣不見了,就像壹頭能撕碎大象的老虎,壹夜之間病得皮包骨頭氣息奄奄,哪裏還有豺狗會懼怕它呢?原先三萬人的戰鬥隊伍,撤往臺灣約五千四百人(對外佯稱萬余人),這部分人都是李彌舊部和大陸老兵,為基本戰鬥骨幹。更多既不願撤臺又不願打仗的官兵,他們采取開小差和不辭而別的方式為自己另找出路。雷雨田說,到1953年底,留在金三角的漢人軍隊只剩下不足六千人。
慘淡經營的時代來臨了。
柳元麟將總部悄悄轉移到江口。面對緬甸政府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他采取的戰略是以退為進,上山打遊擊戰,不與政府軍正面對抗。他們對外改變旗號為“雲南人民反共誌願軍”,當然這種伎倆只是壹個掩耳盜鈴的文字遊戲,“誌願”兩字可以自欺欺人地解釋為地方民間武裝,與臺灣官方無涉。
問題是政府軍吸取前幾次失敗教訓,抓住戰機窮追猛打,大有要把漢人趕下湄公河餵魚的勢頭。柳元麟在壹幅軍用地圖跟前蹙起眉頭,他看到代表緬軍進攻的紅色小旗已經越過孟薩和南果河谷,直接威脅國民黨殘軍的補給線——孟杯機場。臺灣緊急指示:“碼頭決不能丟掉。”機場是殘軍的生命線,壹旦被切斷他們就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幸好緬軍打了幾個勝仗就松懈下來,他們不再集中優勢兵力作戰,而是拉開大網到處清剿,對付走私鴉片和禁毒。這就給了漢人軍隊喘息之機。緬軍的高壓政策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進深山躲避,土司山官都是墻頭草,他們利益受到損害,紛紛派人來聯絡漢人軍隊。這壹來形勢又發生逆轉,戰機出現了,分散之敵就能各個擊破,失去民眾支持的軍隊比聾子瞎子還糟糕。
總指揮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投向窗外高山夾峙的滔滔湄公河。他看見壹只大水板正在艱難渡河,水板上載著馬和人,擺渡水手撐起長長的竹篙同激流搏鬥。他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像那只水板,正被驚濤駭浪所包圍。
柳元麟是侍衛官出身,熟知官場奧秘,卻鮮有機會親臨戰場,因此面對眼前這種錯綜復雜的軍事局勢,他就像壹個名義段位很高卻不善實戰的棋手,眼看機會臨近又沒有把握。從前打仗靠李國輝,現在只有依靠段希文。段將軍是實戰派,又是雲南人的首領,重組後的國民黨殘軍,雲南幫占據絕對優勢,重建四個軍,軍長都是雲南人,隊伍都是雲南子弟兵,這就有些犯了官場大忌,權重欺主,把總指揮柳元麟架空了。問題是即使總指揮有心大搞排除異己,培植親信黨羽,至少現在不是時候,大敵當前,生死存亡更重要。
“忍辱負重,苦撐待變”,這是臺灣蔣介石對他的親訓。柳元麟是個意誌堅強的軍人,不到絕境決不言輸。1962年柳元麟在臺灣石牌家中對記者發表書面講話稱:“……艱苦卓絕,備嘗艱辛,英勇奮戰,報效黨國。大總統有訓:忍辱負重,苦撐待變。余臥薪嘗膽十余年而不逮矣。”
有人在門外喊聲“報告”,進來的是前情報處長錢運周。我從金三角許多老人頗有微詞的敘述中得知,我朋友錢大宇的父親由於告密而投靠柳元麟,大撤臺後被提升為副參謀長。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既要當官就不能顧及良心,官場有官場的鐵律。軍人壹生,不就“賣命”二字麽?為誰賣命不是賣命,不如賣個好主子。“寧為虎狼卒,不與彘羊親”就是這個道理。老長官李國輝已經遠去臺島,他更沒有良心負擔,從此死心塌地效忠柳長官。
錢運周低聲報告:“參加會議的軍官都到了,請總指揮前往出席。”
柳元麟矜持地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壹個副官連忙遞上軍服軍帽,為長官佩上中正短劍,壹行人就向叢林中另壹幢隱蔽的作戰室走去。
4
江口寨裏的老人說,許多年前的湄公河岸上,壹排排新蓋的鐵皮房子拔地而起,像長在山上的樹木。我在當地考察的結果是,房子早已灰飛煙滅,只發現幾處暗火力點,因為年深日久到處坍塌,長出許多荒草來。
將近半個世紀前出席江口高級軍事會議的將領今天大多已經作古,幸存者寥寥無幾,且已被風刮散。我在金三角采訪的雷雨田和楊少甲,他們都已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耄耋老人。我所以對這次會議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是因為已經凝固的歷史向我表明,金三角的戰場局勢由此發生重大改變,鴉片生產和走私呈現上升勢頭,而漢人軍隊的內部爭鬥也因此更加撲朔迷離,呈現出殘酷血腥和妳死我活的幫派特征。
總之我註意到柳元麟時代的金三角正在悄悄發生某種質變。李彌壹統天下,號令三軍,夢想反攻大陸,金三角無人敢與比肩,蔣介石正是因為擔心李彌權力太大才將他軟禁。柳元麟並不是不想做個令行禁止的統治者,反攻大陸的功臣,壹言九鼎,王者至尊,問題是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下面各位實力派軍長不買長官的賬,暗中結成同盟,組成統壹戰線。他們都是雲南人,有共同利益,吸取李國輝做馴服工具的教訓,堅決維護自身利益,對長官軟磨硬抗,實在逼急了就以拉走隊伍相威脅,所以往往令總指揮很頭疼。這就不大像中央軍,而像軍閥割據。事實上從中央軍到地方軍,再到武裝集團和走私販毒王國,這是強大的國民黨漢人帝國由盛而衰,直至被這片古老的金三角土地所同化和消亡的漫長過程。“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我們看到,壹個震驚世界的毒品王國就在逐漸腐爛的國民黨漢人帝國的龐大軀體上生長起來,如同偉大的羅馬神話孕育了愷撒大帝,法蘭西革命成就了拿破侖,奧匈帝國的死亡哺育了希特勒。
在作戰會議上,總指揮嚴厲下達出擊令,對緬軍實施重點反攻,參謀部為此擬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並用密電上報臺灣。但是計劃遭到軍長們的聯合抵制,他們全都不說話,個個裝聾作啞,用沈默對抗權威,因為沒有人願意把部隊交給柳元麟指揮。人人心明如鏡,壹旦交出部隊,也許妳就永遠不再擁有指揮權。
總部空氣好像結了冰,這個場面多少有些令總指揮尷尬,壹屋子部下全都不吭聲,這表明他的陰謀不成功,但是他又不能發火,把軍長撤職或者槍斃,因為總部實際控制的隊伍連壹團人還不到,任何壹個軍長如果要造反,都能輕而易舉把總部消滅掉。
當時有這樣壹個細節,柳長官被沈默冰凍壹個小時,堅冰如故,沒有人出面來解凍,好像大家都在作耐寒比賽。後來有人公然打起哈欠來,壹個接壹個,鼻涕口水都淌出來,這是犯了大煙癮。在重大嚴肅的軍事會議上如此尊容當然很不像話,甚至有藐視長官的嫌疑,問題是這些人沒法控制自己,因為開會時間壹長,他們的煙癮就開始發作,就像肚子餓了需要吃飯壹樣。這些染上鴉片煙癮的將領包括段希文和李文煥,他們終生與鴉片為伍,成為金三角這片土地上最典型的外來開發者和受害者。
不得不暫時休會,不知道是不是鴉片緩和了矛盾,替柳長官解了圍,總之第二天再開會,參謀部宣布放棄聯合作戰的計劃,另擬壹個統壹指揮,分頭作戰的方案。這次軍長們沒有打哈欠,人人情緒高漲,因為分頭作戰相當於搞承包,各自負責,尤其不用擔心長官部壹不留神就把妳的隊伍給搞沒了。大敵當前,軍長們不是沒有責任感,也不是不懂得“唇亡齒寒”、“同舟共濟”的道理,實在是柳長官詭計多端,他們不得不多個心眼,為自己留個退路。
為協調作戰單位步調和統壹行動,大家推舉第三軍軍長段希文作前敵指揮,負責交流情報,傳遞戰況等等。這就等於完全撇開總部,由承包方自己做了主。
據說會後柳元麟不動聲色地向軍長們表示祝賀,預祝反擊成功。只是後來壹個衛士犯了個小錯誤,他不留神將柳長官的愛馬遛傷了腿,惹得長官大發雷霆,當場掏出槍來把他給槍斃了。
5
夜半時分,壹隊黑黝黝的人影急匆匆從孟薩鎮外開來,緬兵崗哨躲在路障後面把槍栓拉得嘩啦響,大聲喝問口令,哪壹部分的?對方用緬語回答:“獵狗行動,操×!老子第十二營的。”哨兵又問:“第十二營兄弟都在山上,妳們回來幹什麽?”黑暗中就有壹個軍官模樣的人走上前來罵道:“老子在山上就不能下來啦?把妳們這些狗×派上山去試試!……老子有任務,快把路障給老子移開!”
哨兵挨了壹通罵,連忙向長官報告。壹個排長光著上身踢踢踏踏地跑過來,手裏提著壹只手電,朝來人亂照壹通。他其實也看不全面,只看見軍官戴上尉肩章,還有些穿便衣的人,有的好像被繩子綁著,有的空著手。對方回答在山上捉到俘虜,要押解到景棟總部去。排長不敢怠慢,命令哨兵把鐵刺拒馬移開。隊伍湧進來,足足有壹兩百人,果然押著壹些漢人俘虜。排長討好地說:“長官,第十二營兄弟要領獎賞了,恭喜恭喜。”
上尉拍拍他的肩膀,遞給他壹支美國香煙,還替他打著火。排長受寵若驚,連忙湊上去點煙,剛剛吸進壹口,腦子裏想好幾句奉承話還沒有來得及說出口,就被人按倒在地,勒住喉嚨拖到壹邊去了。與此同時,崗哨也被下了槍,糊裏糊塗成了俘虜。
上尉軍官就是國民黨殘軍連長坤沙。此坤沙當然已不是新兵坤沙,更不是未來的大毒梟坤沙,他還是個年輕軍官,戰場生活把他鍛煉得從容鎮定。他審問俘虜:“妳們營長住哪間屋子?鎮上有多少兵?”開頭俘虜不肯說,坤沙就亮出壹把匕首,在那個俘虜的褲襠裏拭了兩拭,然後開玩笑壹樣威脅道:“如果妳壹定要閉緊嘴巴,那麽十秒鐘以內妳的雞巴卵蛋就會被割下來餵狗,從此再想做個男人就沒有機會了。”
這壹招果然很靈,俘虜立刻尿了褲子。他看見黑暗中那把匕首像魔鬼眼睛壹樣閃爍著惡毒的光芒。於是俘虜抽抽噎噎地哭起來,把軍事秘密統統交代出來。坤沙滿意地拍拍俘虜肩膀,兩個黑影走過來,坤沙認出是副參謀長錢運周和團長張蘇泉,連忙行舉手禮說:“報告長官,壹切順利,請下命令進攻吧。”
襲擊分三路實施:第壹路由坤沙帶領,直搗緬兵營部。營長貌丁少校正在跟軍官敲竹牌。敲竹牌是緬甸大城市流行的時髦遊戲,類似西方撲克牌,只有十二張牌,擲骰子決定先後,賭博以點大為勝。突然很近的地方響起槍聲,那槍聲清脆得像炒豆子,近得就在窗外,能聽見空彈殼掉在石頭上發出的彈響聲。少校好像被彈簧彈起來,但是沒有等他抓到武器,壹群敵人就撞開門沖進來。他在壹剎那看見襲擊者舉著沖鋒槍,用緬語大叫舉起手來,他不甘心束手就擒,軍官的驕傲和榮譽感驅使他不理會警告繼續撲向武器。沖鋒槍立刻響起來,槍聲震耳欲聾,子彈像蝗蟲滿屋子裏亂飛。緬甸軍官覺得自己好像被壹群發怒的馬蜂包圍,疼痛的感覺像火焰壹樣布滿全身,他還想掙紮,突然壹頭奔跑的水牛狠狠地撞上他,牛角把他挑起來拋向空中。軍官瞪大眼睛,絕望而悲觀地看著敵人的面孔變得模糊起來,槍聲還在響著,但是漸漸遠他而去,世界開始安靜下來。
第二路由團長張蘇泉帶領直撲緬軍兵營。緬兵處處效仿英軍,駐營睡覺不帶武器,武器被集中鎖在櫃子裏,這個軍事教條產生的依據是為了減輕武器對士兵心理的壓力。但是這種人道主義關懷恰恰給襲擊者造成可乘之機。妳想想,睡夢中槍聲突然響起來,人們壹片混亂,因為所有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武器。黑暗中軍官也難免驚慌,壹驚慌就打不開武器櫃,鑰匙被混亂的人群卷走,踩在地上。敵人實行卑鄙的偷襲戰術,而緬兵卻按照西方人的軍事教條,按部就班地做好夢。只有少數僥幸拿到武器的士兵進行還擊,但是大勢已去,絕望的戰鬥進行了十多分鐘就自動停止,光著上身的緬兵向敵人舉起白旗。
第三路由錢運周親自帶領去解救被關在石牢裏的親人。其實土司官寨只有十幾個緬兵,槍壹響他們就逃掉了。士兵們砸開牢門,這間石牢原本是封建土司關押奴才下人的地方,沒想到成為自己的地獄,吃了不少苦頭。錢運周看見妻子瑞娜和兒子錢大宇,還有神情沮喪的土司嶽父像垃圾壹樣擠在角落瑟瑟發抖,他心壹酸差點落下眼淚來。錢大宇後來對我吹牛說,他親手開槍打死壹個緬族軍官,不過我懷疑兩歲的兒童能否拿得動壹支真槍。據說死裏逃生的孟薩大土司壹回到官寨就神氣起來,他粗著嗓子對下人發布命令,咬牙切齒地搞反攻倒算,重新武裝起來的土司兵揚眉吐氣,撣族人將那些作惡多端糟蹋婦女的緬兵俘虜拖出來亂棍打死,翻過去的天又被翻回來。
錢運周對嶽父的報私仇不感興趣,妻子瑞娜不願離開父親,老土司也不願離開他的世襲領地和官寨,女婿應他們要求,留下部分繳獲的槍支彈藥,順便把壹百多個緬兵俘虜也送給土司當家奴。
6
當撣邦高原的太陽從東面山上冉冉升起,田野的霧靄變得輕紗壹樣稀薄,景棟城外的寨子裏就懸浮起壹層朦朧的炊煙來。梳長辮的撣族少女,穿統裙圍頭帕的擺夷大嫂早早趕進城來,她們在石板街道兩旁選好地方,卸下肩上的竹籮,擺出裝有當地調料的小瓦罐,再把頭天備下的肉湯燒得咕嘟咕嘟翻起浪花,熱烈的香味就在清晨的空氣中四溢開來,這時候她們才直起身體,目光安靜地等待顧客光顧。
景棟趕街天,遠近山寨的老百姓都背著藤筐,擔著竹籮,土司頭人神氣地騎著馬,生意人趕著成群的馱牛,或者坐在牛車馬車上,從四面八方趕來交易。自從景棟城駐兵以後,大兵成為當地壹害,軍隊動不動就要抓人,還要搜查戒嚴,搞得人心惶惶。最威風凜凜的當數坐在汽車上的軍官,車門上站著武裝士兵,那種四個輪子滾動的鐵家夥轟隆隆壹過,就跟鬧地震壹樣攪起漫天灰塵,嚇得膽小的老百姓避之惟恐不及,連人帶物跌進路邊的水溝裏。
景棟為東撣邦專員駐地,緬軍總司令部也駐在這裏,軍隊在城外設崗哨,進城要盤查,戒備森嚴。城裏則比較松,雖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巡邏,但是生意照做,日子照過,撣族天生是樂觀開朗的民族,無論世界上發生多大的事情,飯總是要吃的。日子好比流水,河溝裏多幾塊石頭,水不是照樣流麽?
日上三竿,趕街的人群稠密起來,崗哨開始目不暇接。軍隊是石頭,不是流水,所以總有許多空子。壹個黑臉漢子騎壹匹白馬,身後跟著幾個隨從,他們身後還有壹輛嘎吱作響的老牛車,牛車上載著許多鼓鼓囊囊的貨物。漢子穿壹身嶄新的洋綢,戴墨鏡,臉上長著橫肉,很霸道的樣子。他看見哨兵攔住壹群擡棺材的撣族漢子,非要開棺檢查,漢子就慢慢地上前去,也不下馬,拍拍哨兵肩膀。哨兵很蠻橫,槍往上壹指,厲聲說:“妳是什麽人?下馬來檢查。”漢子顯然見過大世面,也不發火,笑笑說:“檢查當然可以,不過今天人這樣多,請長官給壹點面子。”隨從馬上湊上去,塞給哨兵幾張緬甸老盾。
緬兵其實也沒有什麽非檢查不可的規定,不過例行公務,見了眼生的就欺壹欺,得了賄賂就落得做人情,雙方心照不宣。壹行人進了城,選家僻靜的旅店落腳,陸續又有幾夥人進來會合,原來黑臉漢子就是從前李國輝的得力部下,娶頭人女兒做老婆的團長蒙寶業。
城裏探子早把緬兵情報摸得壹清二楚:行政專員公署在東街,有壹排警衛,司令官住在城西兵營,進出都要戒嚴。景棟城共有壹團地方部隊和壹旅政府軍,四門均布有崗哨,緬兵防守十分松懈。司令官雖然行蹤不定,也摸到壹些規律,比如每周要去三次大金佛寺,中午與行政專員共進午餐,晚上常去壹家叫做“千紙鶴”的日本歌舞伎丁,同日本藝伎吹拉彈唱。司令官青年時代曾到日本受訓,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二戰時站在日本人壹邊,人稱“三十誌士”,有很深的日本情結。但是他的警惕性很高,不論再晚都要返回兵營,從不在外面過夜。
漢人團長蒙保業像條陰險的鱷魚,把自己偽裝成壹段朽木潛伏下來窺視獵物。他想在日本伎丁下手,不料壹連兩晚都沒有得逞,目標有重兵保衛,甚至還開來壹輛裝甲車,把伎丁團團包圍,鳥都難以飛過。這個意外情況使蒙團長火冒三丈,他像掉進籠子的老狼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基本上束手無策。好在壹個部下及時貢獻建議,這個部下是當地華僑,熟悉地形,他說往城西兵營去有壹座石頭橋,地形狹窄,等緬兵車隊返回時再打伏擊。蒙寶業順手甩了部下壹個大耳刮子,痛快地罵道:“×老媽!為哪樣不早說?逼得老子差點自殺……幹掉那個雜種提拔妳當連長。”當晚突擊隊進入伏擊地點。這是通往兵營的壹段窄路,部下說得不差,壹座石頭橋,橋頭有個寨子,公路夾在小山包裏,是個打伏擊的天然陣地。他們悄悄埋伏下來,橋頭橫了圓木,只等汽車壹停下來就動手。半夜過後,遠遠看見壹溜移動的白光,那是汽車開來了。隨著汽車駛近,車燈好像巨獸瞪著兩只發光的大眼在夜空中晃動。隊員揭開手榴彈保險蓋,沖鋒槍子彈上膛,如果不出意外,車隊在橋頭受阻停下來,立刻就會有無數手榴彈像吱吱叫著的蝙蝠壹樣從天而降,把汽車炸個人仰馬翻,也許其中壹枚就會幸運地砸在那個大人物頭上。
汽車越來越近,馬達震動空氣,現在不用數都能看清楚,壹共五輛車,首尾相銜地朝他們開來。壹個事先未曾想到的問題突然擺在陰謀分子面前,應該先打哪輛車呢?或者說哪輛車才是大人物的座車呢?他們只有十多個人,分散火力當然會影響效果,所以必須集中力量打擊目標。關鍵在於,哪輛車是襲擊的目標呢?蒙寶業頭上出了汗,他果斷下令,打中間那輛汽車。因為在他看來,前面是開道,後面是保鏢,大官夾中間,這是普遍的道理。
第壹輛車轉眼間開到跟前,人們看清是那輛開路的裝甲車,它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加足馬力沖過障礙。後面的汽車卻攔住過不去,跳下許多士兵急急忙忙來搬路障。蒙寶業壹聲“打”,隊員就把許多黑糊糊的手榴彈用力扔出去,煙霧騰起來,爆炸聲響成壹片,火光映亮夜空。襲擊很成功,兩輛汽車燃起大火,突擊隊趁敵人沒有清醒過來,連忙從小山包後面撤走了。
兩天後,當突擊隊安全返回總部,電臺情報已經發回來。情報說,景棟城裏到處戒嚴,正在搜捕武裝土匪。據悉那晚伏擊之後,兵營裏擡出十多具屍體,其中包括壹名軍官。令蒙團長頓足不已的是,總司令安然無恙,有人看見他出席陣亡者的祈禱儀式。後來查明,大人物僥幸逃脫暗殺的原因是,他居然沒有按照慣例乘坐中間的汽車,而是躲在第壹輛開路的裝甲車裏。
7
史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緬甸政府每年都要發動軍事圍剿,金三角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當然打仗不是政府軍的錯,國民黨漢人始終將金三角當作根據地,像魚兒壹樣躲在森林的大海裏。政府禁毒政策遭到當地人堅決反抗,走私販毒愈演愈烈,政府軍屢遭敗績,所以直到五十年代末,國民黨漢人軍隊依然控制著壹半金三角地區。據情報部門稱,漢人軍隊已經達到壹萬到壹萬五千人,他們打出“雲南人民反共誌願軍”的旗號,化名王胡常的總司令就是從前的副總指揮柳元麟。這個情報令仰光政府憂心忡忡,漢人軍隊入侵的嚴重問題年年都要提上政府內閣的議事日程。
政府在軍事進攻不能完全奏效的情況下,只好借助外交努力,向國際社會控訴國民黨軍隊賴在金三角不走的事實。不料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許多新鮮事物,產生無數新的國際熱點和新聞,人們的目光總是被新鮮的而不是陳舊的事件所吸引,更何況國民黨軍隊已經大批撤離,有西方記者報道和聯合國官員監督作證。臺灣國民黨政府也公開聲明,說如果還有武裝土匪活動,那將是緬甸內政,與臺灣無關。
緬甸政府的控訴不僅沒有受到聯合國應有重視,相反給了壹些老牌帝國主義分子以口實。帝國主義分子說,妳們鬧獨立,自己內政搞不好,可見得妳們緬甸人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國家。這個事實充分說明,野蠻民族鬧獨立是壹個錯誤的選擇。帝國主義分子還奚落說,我們統治妳們國家兩百年,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入侵事件,這不是很好的證明麽?
緬甸政府化悲痛為力量,發動幾次代號為“獵狗行動”、“貝英豪戰役”、“昂山行動”的大規模攻勢,幾乎傾其國家所有,企圖徹底趕走盤踞在金三角的國民黨軍隊,剜去這顆威脅國家和民族安全的毒瘤。令人遺憾的是,金三角地形復雜險要,易守難攻,緬甸政府國力財力十分有限,加之國內政局動蕩,執政的自由同盟分裂,吳努政府岌岌可危,經濟急劇滑坡,危機四伏,民族矛盾壹觸即發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和幹擾了軍事戰略的實施。所以軍事進攻基本上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相反敵人卻從山裏打到平地,從東撣邦打到西撣邦,甚至打出金三角,到1960年,國民黨殘軍已經恢復占領除景棟等重鎮外的金三角大部地區,大有把緬甸政府軍趕出薩爾溫江流域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