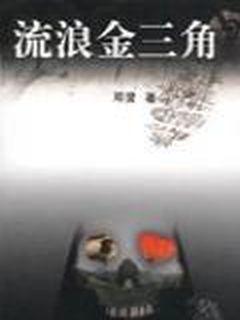-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免費 ] 第二章:《走進金三角》 ...
- [ 免費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費 ] 第四章:《鋌而走險》 ...
- [ 免費 ] 第五章:《背水壹戰》 ...
- [ 免費 ] 第六章:土司招親
- [ 免費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費 ] 第八章:“反攻雲南!” ...
- [ 免費 ] 第九章:撣邦風雲
- [ 免費 ] 第十章:帝國神話
- [ 免費 ] 第十壹章:“旱季風暴” ...
- [ 免費 ] 第十二章:譎波詭雲
- [ 免費 ] 第十三章:大撤臺
- [ 免費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費 ] 第十五章:刀鋒相向
- [ 免費 ] 第十六章:危機四伏
- [ 免費 ] 第十七章:仰光槍聲
- [ 免費 ] 第十八章:兵車南行
- [ 免費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費 ] 第二十章:罌粟王國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末路英雄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龍蛇爭霸》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滿星疊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淵 ...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靈與肉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並 ...
- [ 免費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費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費 ] 第三十壹章:蕩寇誌
- [ 免費 ] 第三十二章:灰飛煙滅 ...
- [ 免費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十八章:兵車南行
2024-4-24 20:40
1
從江口往國軍老機場大約要在叢林中走兩天,是那種真正的亞熱帶原始森林,據說樹木遮天,藤蘿如織,野獸出沒,瘴氣橫行。我很興奮,期待壹次真正的冒險旅行。當然我們不是單獨上路,而是跟隨馬幫行動。這隊馬幫是到三島做柚木生意,也就是說做正經生意,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帶我們壹道上路。馬幫老板是錢大宇親戚,名字叫蒙小業,我沒有見到人,聽說在半路什麽地方等我們。金三角盛產紅柚木,紅柚木是壹種珍稀木材,木質極為堅硬,入水即沈,是東南亞國家民間雕刻工藝品的主要原材料。
早起馬幫上路,幾十匹騾馬逶迤而行,馱著貨物,馬鈴叮當。前面開路是匹老馬,馬脖子上沒有通常的馬鈴,而是在馬頭上掛壹面小鏡子,亮晃晃的,我很奇怪,問有什麽說法沒有?腳夫回答鏡子能避邪,還說這匹老馬走過金三角所有的小路。馬幫沿小路拉開幾百米距離,浩浩蕩蕩,也是壹道景觀。我和向導小米跟在後面,像兩節松松垮垮的拖廂。我騎壹匹棕紅色母馬,是當地矮種馬,與我在孟薩騎的那匹差不多,小米騎匹雜毛兒馬。因為母馬性情溫馴,兒馬脾氣暴躁,所以生手壹般都騎母馬。
很快進入原始森林,山大林密,但是遠沒有想象的恐怖,原因是馬幫所走的小道,幾百年來已被人類的腳步踏成通途。我腳下這條歷險之路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羊腸小道,而是壹條時寬時窄的土路,有些像雲南的牛車道,我認為如果壹輛動力強大的四輪越野車沒準也能轟隆隆地開進去。小路蜿蜒,我們沿著壹條溪谷行進,時而上坡,時而下坡,森林在溪谷兩邊的山頭上,我看見許多白紗壹樣的霧嵐在森林間飄蕩。趕馬人個個沈默,並沒有放開喉嚨大吼山歌情歌什麽的,他們天生似乎就是為了趕牲口和埋頭走路,這與我從國內電影上得到的浪漫印象不大壹樣。馬隊首領是個撣族人,大家稱呼他“馬弄”,我問馬弄大家為什麽不開心?這樣下去人要悶死的。馬弄奇怪地看著我,沒有回答。後來我才知道,大聲說話對金三角趕馬人是壹種禁忌,他們的說法是菩薩不保佑舌頭長的人。
越往後走就開始體會到趕馬人的滋味。時間壹長,馬兒身上出汗,馬汗黏膩膩的像膠水,很快與人體混合在壹起,我身上就多了壹種動物的濃烈氣味,於是我明白為什麽趕馬人身上都有那樣壹種特殊氣味。馬幫規矩,每天吃兩頓飯,早起壹頓,晚上宿營再造飯,白天無論奇書網-整理走多遠妳都得忍著餓。我想別人能忍我當然也能忍,何況腳夫走路,我還騎著馬,問題是我的胃不爭氣,像那些遊手好閑的懶人,吃飽沒事,餓了就鬧意見,而且常常疼出壹身虛汗。我想如果真要遇上險情,比如遭遇野獸,跟土匪搏鬥什麽的,我還有力氣戰鬥嗎?其實這事本來不難解決,提前準備些點心餅幹巧克力,再不濟買幾包方便面,用得著忍饑挨餓嗎?但是馬弄輕蔑地說,偷吃東西(規定時間以外被稱為“偷吃”,奇怪的邏輯!)的人不配做趕馬人,他會被逐出馬幫。
我體會這大概是壹種幫規,相當於軍隊紀律,有人吃東西,有人挨餓,難免影響軍心,所以幹脆大家都不許吃。
下午三點多鐘在壹個地名叫做白花箐的傈僳族寨子外面宿營,我不明白馬幫為什麽早早就休息,得到回答是,馬兒要吃草,所以人就得休息。
這天晚上,我吃到壹頓真正意義上的金三角的野餐。趕馬人在石頭上支起鍋,拾來樹枝生火煮飯。馬弄從馱架上取下壹只鐵筒,打開油布蓋子,掏出壹坨黑糊糊的東西扔在鍋裏。當開水翻滾起來,壹股熟悉的惡臭味直沖腦門,我快樂地嚷起來:“我從前吃過這種東西!”
馬弄驚奇地說:“小漢人(當地人對華人統稱),妳吃過煙籽豆腐?”
我不想告訴他為什麽,自己的事情,不壹定非要別人知道。我等待著,果然不壹會兒湯鍋裏臭味消失,飄出陣陣香味。我迫不及待嘗壹口鮮湯,心快樂地怦怦直跳。我對馬弄說,妳知道為什麽煙籽豆腐美味可口嗎?其實多數植物種子都是油料作物,鴉片煙籽也不例外。用鴉片煙籽腌制食品,早在中國唐代就有記載,宋代稱“禦米”,貴為宮廷食品。蘇東坡詩雲:“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湯就是罌粟籽煎湯。
馬弄嘟噥道:“我才不管妳們漢人怎麽說,我們祖祖輩輩都這樣吃。”
夜裏露宿野地。火堆增加到好幾個,而且都添加圓木,火燃得旺旺的。腳夫取出蓑衣就地鋪下,他們聚在壹起抽煙,我從空氣中漸漸散開來的壹股可疑的香甜氣味中突然意識到,他們是在抽大煙!果然,我看見他們將大煙與生煙絲摻在壹起,然後湊在竹煙筒上輪流抽,這種方法當地稱“舵把筒”。在金三角,抽大煙是件平常事,沒有人大驚小怪。
我還註意到,騾馬被趕到壹起吃草料,貨物堆在火堆中央,這種古老的宿營方式跟錢大宇說的沒有兩樣,只是沒有人值夜班。我心裏忐忑不安,為什麽不安排人站崗呢?萬壹來了野獸怎麽辦?就是偷馬賊牽走幾匹騾馬也是壹大損失啊!但是既然馬弄不安排站崗總有理由,他們是主人,我只好客隨主便。
這壹夜睡得不踏實,山很大,樹很密,營地卻很安靜,只聽見溪水淙淙流淌。我想象老虎黑熊偷偷走近馬群,或者窺視睡覺的人,還有那些專門偷盜馬匹的盜馬賊,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這裏畢竟是金三角叢林,不同於旅遊勝地或者森林公園,壹想到強盜手提大刀嗷嗷直叫的模樣,我就神經緊張。不知白天吃了什麽不幹凈的東西,夜裏起來拉肚子,趕緊吞下幾粒黃連素,下半夜我才昏昏地睡過去。好像剛打個盹,壹睜開眼睛天已經亮了,趕馬人都在收拾馱子,飯也做好了,這說明我昏睡時什麽驚險故事也沒有發生。
我站起身來活動壹下筋骨,在這個大自然懷抱深處,在充滿傳奇色彩的金三角原始森林的馬幫營地,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終於度過平安壹夜,並且準備站起身來去溪水裏漱口洗臉。
這時候我看見壹個不認識的人伸出手,迎面向我走來。
2
關於泰國商人蒙小業先生,我想讀者並不陌生。
蒙小業的父親就是原國民黨師長蒙寶業,母親是孟薩頭人的女兒,與錢大宇母親有遠親關系。錢大宇答應介紹我們認識,但是蒙老板到處奔波做生意,所以壹直沒有機會見面。
蒙小業同錢大宇壹樣,有壹半中國血統,但是他的出生地卻在中國芒市,距離我當知青的隴川縣只有不到壹天的路程,所以他應該自然取得中國國籍。關於他的出生經過本身就是壹部戰爭小說,準確說他還在母親肚子裏就成為俘虜。
我們互相握手,寒暄幾句,原來蒙老板趕了壹夜山路,專程從寮國會曬趕來同馬幫會合。短短幾分鐘,我對這位泰國商人有個初步印象:豪爽、精明、果斷、雷厲風行,不像那些斤斤計較的白臉奸商,倒像個走南闖北的江湖好漢。我想這種氣質大約來自他職業軍人父親的血統遺傳。
蒙小業有壹支手槍,他帶了三個保鏢,每人壹支沖鋒槍,不過都藏在雨衣裏面。我問他這是為什麽?蒙老板答:“在金三角,除了做毒品的走私馬幫,壹般商業馬幫不用擔心搶劫,因為柚木在山裏並不值錢,誰也不值得為這種生意流血。”我說:“妳為什麽要帶槍,妳販毒嗎?”他看我壹眼,笑笑說:“妳這話是犯忌的,我不販毒,但是我不敢說我沒有仇人,金三角任何事都是防不勝防的。”
在這個叫做白花箐的地方,果然到處白花如雲,白花長在大樹上,迎風飄雪。據說這種花可以做菜吃,但是得先放在鍋裏煮,把水倒掉,不然會中毒。當馬幫走在山道上的時候,正是白花開放的季節,風壹刮,花瓣如鵝毛大雪漫天飛舞。腳夫依然埋頭走路,馬兒依然逶迤而行,在這樣壹種花海如潮的壯麗背景下,馬幫的艱苦生活反襯出壹種原始的浪漫情調,但是腳夫個個面無表情,熟視無睹的樣子。我想是艱苦的生活把人變得麻木不仁。不壹會兒我感到渾身不自在起來,脫下衣服壹看,原來皮膚過敏,身上脖子上起了許多紅皰,奇癢難耐。加上夜裏腹瀉未止,腸鳴如鼓,看樣子真是禍不單行。我擔心如果病倒的話,別說采訪,就是馬幫也不能留下來陪妳啊!這是什麽地方?金三角!妳能獨自留在大山裏麽?誰替妳醫病呢?我甚至有些慌張,恨自己不爭氣,偏偏關鍵時候病了,如果考慮周全,應該多備壹些藥,問題是現在後悔沒有用,後悔不能當藥吃。在這個絕望的時候,蒙小業安慰我說:“不要緊,我有萬靈藥水,包妳馬上跟好人壹樣。”
我對他的話將信將疑,什麽萬靈藥水,沒準是什麽巫術之類,要是商人也能治病,豈不人人都成了醫生?我是堅定的唯物論者,從不信邪。蒙小業讓馬弄取來指甲大小壹塊生鴉片,用水溶在碗裏,發出臭烘烘的氣味,看上去跟泥湯差不多。我猛然記起馬鹿塘那位婦女餵咳嗽老者的藥湯,還有那些接生婆向難產婦女灌下的黑色藥水,看來都是這種所謂的萬靈藥水了。蒙小業說:“這是生膏水,妳喝下準會好的。”我堅決搖頭說:“無論什麽神仙水我也不喝。”蒙小業說:“我知道妳不相信它,其實在金三角,生膏水是我們祖祖輩輩治病的良方。妳不試試,怎麽知道沒有用?”
蒙小業最後壹句話起了作用。壹個有勇氣進入金三角的作家是不該拒絕體驗的。六十年代,壹位名叫艾拉的美國女科學家為了進行科學研究,在南美叢林中與黑猩猩共同生活了三十年,這是何等令人肅然起敬的獻身精神!金三角人祖祖輩輩以鴉片水治病,這從壹個側面說明鴉片與當地人生活的重要關系,妳不能親口嘗嘗怎麽知道梨子的滋味?妳的勇氣到哪裏去了呢?
我鼓足勇氣,在眾目睽睽之下把那碗看上去讓人惡心的臟水吞下去,連那些沈澱物也沒有剩下。我絕望地想自己沒準會當場嘔吐,腹疼加劇,吐得上氣不接下氣。沒想到我的腸胃似乎並不排斥生膏水,很快肚子裏有了壹種細雨潤物的很溫暖很熨帖的感受,放出幾個臭屁來,腹瀉居然止住了,人也有了精神。更妙的是,皮膚過敏也不再折磨我,第二天睡覺起來,紅皰完全平復痊愈。
我問蒙小業:“鴉片為什麽有這種奇效?”
他說:“我怎麽知道?反正幾百年來當地人這樣治病總有他們的道理。”
我總結說:“這就有些像中醫,西方人莫名其妙,什麽望聞問切,像搞迷信活動,但是很多醫學奇跡都是中醫創造出來的。”
蒙小業笑笑說:“可能吧。”
我問:“會遇上販毒武裝嗎?比如在這條道上?”
他搖搖頭說:“販毒路線壹般在深山裏,秘密通道,外人不知道,當然不排除他們有時也借商業通道過路。販毒武裝前面有探子,稱‘馬竿’,看上去像采藥人或者打獵的,遇有馬幫,馬竿會發信號給後面,讓他們及時避讓。”
我感到壹絲失望,我說:“聽說這壹帶有坤沙殘部在活動,妳做生意不危險嗎?”
他回答:“危險當然是有的,但是壹般來說金三角有自己的規矩,打個比方,就是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除非政府軍進來打仗。”
我說:“政府軍進來打仗又怎麽樣?”
他說:“那就等於秩序被破壞了,成了壹場混戰。政府軍剿毒,他們分不清誰是毒販,誰是良民,所以幹脆不問青紅皂白,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毒販。當然事實上誰也沒法弄清楚毒販與販毒的區別。”
我驚訝地說:“毒販……與販毒,此話怎講?”
他狡黠壹笑,說:“金三角人人都是良民,但是人人都可能販毒。然而真正的毒販只是少數。”
我說:“比如妳呢?”
他大笑,說:“貧困比毒品更可怕,妳明白嗎?”
我不同意,認為他是詭辯。我反駁說:“妳知道毒品害了多少人?”他回答:“我天天滿世界跑,這點知識我還是有的。”我說:“那麽妳販毒嗎?”他作出驚訝的樣子回答:“我不是做正經柚木生意嗎?”我說:“妳不是說人人都可能販毒嗎?”他想想回答:“我指那些正在販毒的人,因為他們比我窮。”
這天我們在山道上走了壹百多裏路。當晚我們到達國軍老機場所在地孟杯,孟杯是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小鎮,壹條坑窪不平的簡陋街道向我們展示金三角腹地的貧困落後。是夜馬幫按照當地習俗在鎮外宿營,我們則住進鎮上的小旅店。
3
許多年後的蒙小業常常做著這樣壹個夢,他的漢人父親,國民黨師長蒙寶業騎壹匹膘肥體壯的大黑騾子,從金三角的山道上匆匆地奔馳而來。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父親沐浴在殘陽夕照中,春風得意,馬蹄生輝。當然這是壹種意識流,因為那時候泰國商人蒙小業尚未出生,準確說還懷在撣族母親肚子裏,他母親就是前孟薩頭人的女兒籲罕姑娘,漢撣和親的犧牲品。他向我勾畫這幅春風馬蹄圖的時候,我仿佛看見那位籲罕姑娘已經像個風幹的木乃伊。他說那壹天他父親正從壹個遙遠的地方向他走來,他們父子只差壹個月時間就將在這個充滿動蕩不寧的世界上骨肉團聚,然而他父親始終沒能走完這段山路,所以這幅圖畫只好反復出現在兒子的夢境中。
蒙寶業,廣西陸川人,畢業於中央軍校貴州獨山分校,參加過兩次入緬抗戰和反攻滇西戰役,為譚忠老部下,開創金三角的元老之壹。李彌時代,譚忠受排擠,李國輝遭冷遇,蒙寶業自然無所作為。李彌去臺,大權旁落,蒙寶業終於從權力鬥爭的夾縫中出了頭,升任手握大權的第二師上校師長。他指揮的第二師號稱五千人馬,其實也就壹千多人,占據離中緬邊境最近的累班鬧山脈幾個富庶壩子,軍官清壹色為原九十三師老部下,師部駐地三島。蒙寶業大做走私生意,他的地盤正好是金三角主要鴉片產區,所以別人背後送他壹個外號“鴉片師長”。
其實並非蒙寶業偏愛鴉片,用他兒子的話說就是“不得已而為之”。壹個軍人,沒有政治目標,沒有國家利益和奮鬥方向,惟壹緊迫的事情就是養活自己,這不跟土司兵山兵土匪沒有區別嗎?反過來說,在金三角,壹支流亡的軍隊不演變成土匪又能變成什麽呢?
曾經被臺灣報紙譽為反共英雄和熱帶叢林戰專家的國民黨師長蒙寶業,這天騎著壹匹大黑騾子,身後緊跟壹班警衛,個個都騎騾子,挎美式卡賓槍,威風凜凜前呼後擁地穿山過寨,趕回那個地名叫做三島的師部駐地。
三島不是三座島,撣語意為三個漢人官家管轄的地方,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官家,只有蒙寶業是三島的太上皇。蒙寶業滿面紅光,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他的滿足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蒙師長大喜之事有二:壹是老婆籲罕懷胎九月,孫大仙算過命,是個兒子,這是他的頭生兒子。二是他剛剛被蔣介石招到臺灣授勛,國防部長授予他陸軍少將軍銜,從此他就是將軍了。榮升將軍是每個軍人的夢想,盡管授銜的不止他壹人,蔣總統分明也沒有特別記住他,蒙寶業回到江口還是對柳總指揮說了許多感恩戴德的話。其實他心裏很清楚,他所以得此殊榮決非對臺灣做出多麽巨大的貢獻,而是柳總指揮不得不拉攏他。
在江口,柳元麟當頭給他潑了壹盆冷水。
柳元麟說:“第壹敵人肯定要進攻,做好戰鬥準備。第二總部決定收縮防區,三島由第五軍接替,第二師轉移到總部待命。”蒙寶業在心中大罵:媽的×,誰也別想打老子的主意!老子哪裏也不去,敵人來了就跟他們在大山裏打遊擊!如果放棄三島,誰出經費養活老子,誰替老子收大煙糧食!再說與總部挨得那麽近,不定什麽時候姓柳的說變臉就變臉,呂維英甫景雲就是下場!
來到駐地,他先回三島寨子看了太太籲罕,籲罕挺著大肚子迎接丈夫。蒙寶業與其說愛太太,不如說更愛太太肚子裏的兒子,太太已經替他生了兩個女兒,但是沒有兒子就絕了後,這是他的壹塊心病。父親把頭貼近兒子,父子倆隔著壹層薄薄的肚皮交談。兒子聽見父親說:兒啊妳快出來,老子想妳快想瘋了。兒子回答:老爸妳再耐心等等,兒子不會讓妳失望的。
後來父親出了門,沒有去師部而是悄悄來到六團召集軍官秘密開會。他所以避免直接回師部,是因為壹年前柳元麟以臺灣國防部名義向各軍、師派遣特派員,名義上是政治部主任,實際上是安插特務,專幹告密策反的壞事。派給他的政治部主任名字叫邱裏,中校軍官,擅長搞陰謀詭計。這壹招的確很毒辣,等於在他身邊安放了壹顆定時炸彈。只有第三、五軍態度強硬地抵制總部派來的政治軍官,段希文自己任命政治部主任,李文煥跟著效仿,柳元麟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無可奈何。
與會者都是師長的心腹,大家壹致認為不能服從總部的命令。副師長是他的老搭檔,專管鴉片收稅,他算了壹筆賬,如果放棄三島,單單稅收壹項就將損失多少多少,部隊經費只夠維持三個月,往後勢必坐吃山空。而今年大煙長勢格外喜人,到嘴的肥肉怎麽能夠放棄呢?參謀長也在三島娶了當地太太,對總部命令表示不滿,所以與會者達成壹個共識,就是軟磨硬抗,也要找出種種理由拖延時間,反正就是不予執行。壹旦國境對面果然有情況,立即采取兩套作戰方案:利用地形跟敵人周旋,分散上山打遊擊。
傍晚時分,蒙寶業開完秘密會議回師部去,他騎在黑騾子上,心情很是怡然舒暢。他身後跟著壹隊人馬,放眼望去,三島壩子天高地闊,山清水秀,遠近山坡上,燦爛的罌粟花正在怒放,猶如五彩雲霞鋪落人間。壹群飛鳥鳴叫著從頭頂飛過,潮水般的幽香隨風飄來,湧動在半透明的空氣中。剛剛晉升將軍的蒙寶業躊躇滿誌,他抽抽鼻子,覺得花香醉人,連三島的空氣也醉人。他是軍人,不是花前月下的詩人,但是他酷愛罌粟花,這種花香勝過世界上任何最美好的氣味。花香意味著豐收,意味著財源和收入,罌粟是部隊的命根子,也就是他的命根子。金三角,多好啊!天高皇帝遠,猴子稱大王,他是這片土地的主人,沒有人敢於拂逆他的意誌。許多年後蒙小業對我說,他父親的官道註定走不通,因為他眉心有顆短命痣,孫大仙說過那是血光之災,躲不過的。
山道拐個彎,前面壹片小樹林,中間壹株大青樹,華蓋如傘,鶴立雞群。蒙師長看見大樹下拴著壹匹棗紅馬,馬旁站著壹個人,這人穿壹身美式軍服,很悠閑地玩弄壹根鑲銀馬鞭。他心中壹驚,只聽見那人對他笑道:“師長回來了,歡迎歡迎,祝賀榮升將軍……妳們那個會,到底開完了?”
蒙寶業的笑容在臉上凝固了,他認出這人正是臺灣派來的特派員,政治部主任邱裏中校。特派員好像他的影子,無處不在地跟著他,甩都甩不掉。當然他暫時不想與他鬧翻,特派員畢竟是上面的人,來頭很大,因此蒙師長只好裝聾作啞,含糊其詞地企圖蒙混過關。不料特派員上前拉住騾子韁繩說:“請師長對我說明,妳們背著我開了什麽會?否則我立即就向總部匯報。”
如果蒙寶業沒有當上將軍,沒有到臺灣接受蔣介石接見,如果當上將軍的蒙寶業沒有對總部不滿,沒有抗拒命令的念頭,他恐怕就會忍壹忍,小不忍則亂大謀,退壹步天地寬嘛。問題是現在他是將軍了,將軍有自己的尊嚴和脾氣,所以他終於勃然大怒,掏出手槍在特派員頭上重重敲了壹下,警告他說:“妳滾開,我是這裏的長官。聽口令,否則老子槍斃妳——立正!向左轉,開步走!”
鮮血從特派員頭上流下來,蒙寶業騎著騾子得得地走過去,蒙小業聽見他老子在心裏惡狠狠地發誓:“老子造反的話,第壹個就宰了妳!”
4
公元1960年的雨季終於在壹陣緊似壹陣的幹風中漸漸遠去,壹夜之間,擠壓在山頭上的潮濕雲團好像被傳說中那個巫婆的魔袋收走了,山林挺直胸膛,天空變得高遠而明亮。太陽壹露頭,就將那種壓抑已久的澎湃激情轟轟烈烈地釋放出來。湄公河水退下去,沙灘從水中爬出來,撐筏的吆喝聲回蕩在寧靜的河面上。由於地面水分在灼熱的空氣中蒸發,山林終日浮遊著壹層牛乳般的白色霧嵐,好似阿拉伯少女的面紗。泥濘道路變得幹燥而堅硬,果實因成熟而腐爛,種子得以播入泥土。
在這個陽光充足和大地收獲的季節裏,戰爭陰影卻像逼近的沙暴黑雲壹樣壓迫在人們心頭上。戒備森嚴的國民黨江口總部,情報紛至沓來,北方邊境線上,敵人大軍雲集,可以肯定這些敵人的野戰部隊決不是擺在哪裏做做樣子的。西線情報稱,緬軍兵力已經增加到三萬人,三個步兵旅,九個機械化營,沿東枝鐵路渡江東進,準備大舉進攻。
總指揮柳元麟苦著臉研究壹份重要情報,情報稱,北方在邊境劃定壹片“紅線區”,嚴禁作戰部隊越線。
他在這段話下面劃了幾個重重的問號。為什麽要劃出“紅線區”?兵不厭詐,這是不是敵人施放的煙幕彈?壹個以假亂真的花招?西線緬軍並不足懼,就是他們數量再多些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來自北面的老對手。問題是,他們為什麽不直接攻擊江口總部和孟杯機場,與緬軍形成戰略合圍之勢,這樣的話,金三角國民黨的天就塌下來了。他想不通的是,他們為什麽要劃出“紅線區”來縛住自己手腳呢?這不是給對手留出很大的回旋空間嗎?
他問副參謀長錢運周:“妳看這份情報可靠嗎?”
錢運周謹慎回答:“不排除是個迷惑我們的陰謀,需要加以證實。”
總指揮沈吟壹會兒說:“假定這份情報可靠,妳看我們該怎麽辦?”
錢運周更加小心,他知道總指揮是個疑心很重的人,而且獨斷專行,不大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他揣摩長官的意思,對究竟怎樣作戰拿不定主意。他回答說:“假定情報可靠,我建議利用這個紅線區,集中力量重創緬軍,消滅其有生力量,讓仰光政府今後不敢輕舉妄動。如果紅線區是陰謀,我們應該放棄金三角,全面撤退到寮國去,不與敵人正面對抗。”
柳元麟沒有說話,他在作戰地圖前站了許久,然後問:“對緬軍作戰,參謀部有具體計劃嗎?”
錢運周預感到總指揮要下決心打大仗了,他恭恭敬敬回答:“是的,參謀部早就擬定對付緬軍作戰方案,包括與緬軍主力決戰的‘零號方案’。”
柳元麟轉過身來,錢運周看見長官眼睛發亮,這是職業軍人對戰爭的渴望。長官說:“與緬軍主力決戰有把握嗎?”
副參謀長立正回答:“報告長官,‘零號方案’經過反復實地勘察論證,應該有把握實施。”
柳元麟點點頭說:“很好,我們看似被動,其實主動,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且看敵人如何動作。具體說就是且看北面敵人如何動作。”
錢運周說:“我立即派人加強情報收集,嚴密監視國境對面的動靜。是否催促蒙寶業第二師盡快向南撤退或者轉移?”
柳元麟沒有說話,取出壹份電報扔給錢運周,那是第二師政治部主任邱裏密報蒙寶業密謀造反,散布什麽“寧可被共軍消滅,也決不撤離三島”之類蠱惑人心的流言,建議總部火速逮捕第二師軍官,整肅部隊。雲雲。
錢運周覺得背上有冷汗出來。他當然明白蒙寶業不會造反,這個“鴉片師長”是拿三島當命根子,不肯撤出那個富庶的鴉片之鄉。可是告密者這種險惡用心讓人不寒而栗心驚肉跳。柳元麟問他:“妳怎麽看,蒙寶業會不會造反?”
錢運周硬著頭皮回答:“蒙師長是國軍元老,又剛剛被大總統接見,晉升將軍,黨國對他恩重如山,我想他不敢起謀反之心吧。”
柳元麟冷笑道:“莫非邱裏謊報軍情不成?”
錢運周不敢正面回答,他顧左右而言它:“民國三十九年(1950),蒙師長滇南阻敵,與數倍共軍激戰三晝夜,掩護主力安全撤退……”
柳元麟冷笑著打斷他的話:“小錢,妳同我耍花槍啊。我知道妳跟這個蒙寶業是什麽親戚對不對?……實話告訴妳,就是給他六個膽子諒他也不敢造反,他只是要做地頭蛇,保住那塊地盤。我不派去那個邱裏,他不是更加為所欲為了嗎?”
他隨即口授兩道命令:壹道是申斥邱中校僭職越權行為,給予警告處分。另壹道是命令第二師做好阻擊北面敵人的戰鬥準備。
金三角國民黨殘軍像頭狡猾多疑的狐貍,壹面盯著眼前走近的獵物,壹面防備天敵克星的出現,期盼那道“紅線區”奇跡般生效。
5
蒙小業說,那天晚上他父親夢見壹頭大蛇遊來,大蛇頭如小丘,眼如燈籠,只壹吸就把黑騾子吸進肚子裏。父親嚇得兩腿發軟,知道自己遇上蛇精,掏出槍來連連射擊。誰知子彈被那畜生只壹吸,都吸進肚子裏不見了。父親想自己英雄壹世,剛剛晉升將軍,落得如此下場,就傷心地哭起來。誰知這壹哭竟哭醒過來,他連忙把太太叫醒,太太當然也弄不明白這個兆頭是兇是吉,就對他說請孫大仙來占個卦。
關於這位被尊為大仙的孫巫師,我先前並未在意,後來偶然聽人說到孫大仙本名,這才不由得大吃壹驚。原來此人居然不是蠅蠅茍茍的無名鼠輩,而是壹個曾經大名鼎鼎,在中國現代史上曇花壹現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變”壹舉改變中國社會的歷史方向,壹位軍官親手從華清池的假山背後捉住蔣介石,轟動全國,這位壹舉成名天下聞的軍人就是張學良將軍的衛士營長孫銘九。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在南京被扣,東北軍解體,這位孫營長從此銷聲匿跡不知下落。我想蔣介石對這位孫營長壹定印象深刻,所以小人物的消失總是有充足理由的。而當我1998年走進金三角才驚訝地發現,孫銘九居然逃過死神魔爪,輾轉流落到金三角,這真是壹個命運的奇跡。
當地人說,孫大仙專替人算命看相,消災解難,據說看得很準,能預蔔生死未來。有人問他:可知自己生死後事?答曰:死無葬身之地。事實上他的下場果然很悲慘,被人扔下毒蛇洞,印了死無葬身之地的說法。
已經得道成仙的孫銘九端坐在蒲團上,細聽蒙寶業訴說噩夢由來。蒙小業父親年輕時並不信命,吃兵糧的人,只信槍桿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可是隨著成家立業,當上將軍,隊伍多了,家私大了,這才開始信神信命,而且惟恐不夠虔誠。他家中至少供奉了三尊外面請來的各路神仙:如來佛祖,關公大帝,趙公元帥。神仙來路不同,用處也不同,如來領導未來,人難免壹死,到另壹個世界不會下地獄。關公是勇武之神,保佑軍人打勝仗。趙公元帥是財神,只要他老人家高興,就會把錢大把扔進妳的口袋裏。
大仙聽完噩夢,長嘆壹聲說:“不瞞將軍,妳眼前有血光之災呀。”
蒙寶業忙請大仙指點迷津。大仙起身在院子裏打了壹卦,指出禍將北來,不過他已經請動關帝半路顯靈,消弭這股惡煞之氣。蒙寶業大吃壹驚,難道大仙連軍事秘密都能預知?但是孫大仙不肯泄漏天機,只是鄭重指點,十日之內不宜遠行,封閉朝北的門窗,改從南門出入。如不遵循,定有殺身之禍降臨,雲雲。
蒙寶業送走大仙,參謀送來急電,指揮部通報敵情,命令南撤十公裏,情報說第二師將是敵人閃擊的首要目標。蒙寶業放下電報,他看看窗外藍藍的天空,碧綠的大地,陽光亮閃閃地穿過葉縫,像織出道道金線。山坡上罌粟花燦爛開放,再過半月就要開始割大煙,他們為什麽要撤退呢?他忽然覺得敵情通報不真實,敵人還沒有發動進攻,他們有必要驚慌失措嗎?放棄到手的大煙,下半年部隊吃什麽?靠什麽發薪餉?再說孫大仙有言,十日內不宜遠行,於是他發布命令:壹團向北展開警戒,二團向南展開警戒,師部和直屬隊原地不動。
壹連數日平安過去,邊境情報站和警戒哨都沒有發現異常動靜。蒙寶業壹顆懸起的心漸漸放回原處。他遵循大仙囑咐,將屋子門窗壹律改向南開,並在心裏暗暗祈禱,菩薩保佑,只要大煙開割,收完這壹季,躲過這壹災,他蒙寶業壹定給菩薩重塑金身。
這天他照舊在師部值班,騎騾子到處巡視,晚上跟參謀長打牌喝酒,後來突然想起幾天沒有回家,不知老婆肚子裏的兒子怎麽樣,這才囑咐值班軍官,然後頭重腳輕回家去睡覺。原本摸慣房門,不料壹頭撞在墻上,額角上起個包,這才記起房門已經改了方向。
太太籲罕還沒有睡覺,聞見丈夫身上散發的濃重汗味和酒味,知道丈夫又喝多了。撣族女人是男人的奴隸,這壹點很像日本,越是好女人越是好奴隸。太太趕快起身服侍丈夫,直到丈夫在床上打起鼾來。蒙小業說,這個時刻很重要,因為他在母親肚子裏突然聽見槍聲。
槍聲是從寨子外面的師部響起的。震耳的槍聲把整個寨子都驚醒了。蒙寶業壹聽見槍聲就醒過來,他側耳壹聽,沖鋒槍在猛烈射擊。槍聲令他魂飛魄散,敵人果然不聲不響摸進來了,他也顧不上太太和尚未出生的兒子,翻身下床撲向窗口。他的意圖本來很清楚,打算像頭靈巧的山貓或者鹿子縱身壹躍,躥出窗外去,窗外到處都是茂密的灌木叢,因此他就會像魚兒遊進大海壹樣消失。沒想到黑暗中他卻被壹堵冰冷結實的墻壁重重地彈回來,這壹撞是如此沈重,槍也丟掉了,頭也撞暈了,眼冒金星,躺在地下半天起不來,原來他竟忘記自家門窗都改向南邊了。將近四十年前蒙小業與他大腹便便的母親壹道親眼目睹這個悲慘的事實,但是他們顯然都對這個昏頭昏腦陷入困境的笨重男人無能為力。等他終於掙紮爬起來,襲擊者已經闖進家門,雪亮的手電筒光罩住他。
“蒙寶業,妳必須老老實實……優待俘虜,否則自取滅亡!”襲擊者用清楚的漢語警告說。蒙寶業停止反抗,他對這種警告方式真是再熟悉不過,誰要是受到警告,說明妳已經被死神咬住喉嚨。他乖乖站身起來,像嬰兒那樣無助而可憐地看了女人壹眼,太太嚇得只會哭泣,肚子裏的兒子跟著母親壹起顫抖。這個父親謙卑地對襲擊者懇求:“請千萬不要傷害……女人,她快要生孩子了。”
可以想象,這天夜裏三島變成壹座煉鋼爐,寨子裏到處鋼花飛濺,到處都在起火,都在熊熊燃燒。蒙寶業被押著往外走,同蒙寶業壹道走出寨子的還有女人和女人肚子裏的兒子。兒子認為父親壹定後悔得想自殺,十天不出門就等於自取滅亡,但是誰叫妳相信巫師的壹派胡言呢?而他那些混賬部下,竟然連壹個警報都沒有發出來就讓師長做了俘虜。
總之從這天起三島的天就塌下來,蒙寶業和他的家庭以及這支番號為國民黨第二師的部隊陷入沒頂之災。當俘虜押出寨子,踏上山道,彌漫在金三角土地上的罌粟花正在熱烈開放,花香還是那麽濃烈,空氣還是那麽醉人,這對蒙小業的軍人父親來說好像是種大膽鼓勵,是種深情挽留。蒙太太最後看到丈夫是在壹座山崖邊,丈夫突然像豹子那樣躥起來,壹連撞倒幾個人,然後滾下路邊深谷。這是充滿絕望和瘋狂的反抗,因為俘虜手臂被捆綁著,基本上沒有成功逃跑的可能。蒙小業說,當槍聲猛烈地響起來,母親壹下子就癱倒在地上,這個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男人從此被黑暗吞沒,從他們的生活中永遠消失……
6
壹夜之間,對手神話般出現,鐵錘砸在蒙寶業第二師頭上。柳元麟緊急下令各部隊放棄陣地,脫離紅線區靜觀戰局發展。
此後數日,第壹、二軍均與之接觸,交火後快速後撤。
在壹片近於窒息的等待和心跳中,奇跡果然發生,代表敵人的紅色小旗果然停留在紅線邊緣上,不再越雷池壹步。幾乎同時,西線情報飛來,大批緬兵渡過薩爾溫江,在飛機掩護下沿景(棟)大(其力)公路向東推進,已經與三、五軍前哨接上火。
決戰開始了。
從江口往國軍老機場大約要在叢林中走兩天,是那種真正的亞熱帶原始森林,據說樹木遮天,藤蘿如織,野獸出沒,瘴氣橫行。我很興奮,期待壹次真正的冒險旅行。當然我們不是單獨上路,而是跟隨馬幫行動。這隊馬幫是到三島做柚木生意,也就是說做正經生意,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帶我們壹道上路。馬幫老板是錢大宇親戚,名字叫蒙小業,我沒有見到人,聽說在半路什麽地方等我們。金三角盛產紅柚木,紅柚木是壹種珍稀木材,木質極為堅硬,入水即沈,是東南亞國家民間雕刻工藝品的主要原材料。
早起馬幫上路,幾十匹騾馬逶迤而行,馱著貨物,馬鈴叮當。前面開路是匹老馬,馬脖子上沒有通常的馬鈴,而是在馬頭上掛壹面小鏡子,亮晃晃的,我很奇怪,問有什麽說法沒有?腳夫回答鏡子能避邪,還說這匹老馬走過金三角所有的小路。馬幫沿小路拉開幾百米距離,浩浩蕩蕩,也是壹道景觀。我和向導小米跟在後面,像兩節松松垮垮的拖廂。我騎壹匹棕紅色母馬,是當地矮種馬,與我在孟薩騎的那匹差不多,小米騎匹雜毛兒馬。因為母馬性情溫馴,兒馬脾氣暴躁,所以生手壹般都騎母馬。
很快進入原始森林,山大林密,但是遠沒有想象的恐怖,原因是馬幫所走的小道,幾百年來已被人類的腳步踏成通途。我腳下這條歷險之路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羊腸小道,而是壹條時寬時窄的土路,有些像雲南的牛車道,我認為如果壹輛動力強大的四輪越野車沒準也能轟隆隆地開進去。小路蜿蜒,我們沿著壹條溪谷行進,時而上坡,時而下坡,森林在溪谷兩邊的山頭上,我看見許多白紗壹樣的霧嵐在森林間飄蕩。趕馬人個個沈默,並沒有放開喉嚨大吼山歌情歌什麽的,他們天生似乎就是為了趕牲口和埋頭走路,這與我從國內電影上得到的浪漫印象不大壹樣。馬隊首領是個撣族人,大家稱呼他“馬弄”,我問馬弄大家為什麽不開心?這樣下去人要悶死的。馬弄奇怪地看著我,沒有回答。後來我才知道,大聲說話對金三角趕馬人是壹種禁忌,他們的說法是菩薩不保佑舌頭長的人。
越往後走就開始體會到趕馬人的滋味。時間壹長,馬兒身上出汗,馬汗黏膩膩的像膠水,很快與人體混合在壹起,我身上就多了壹種動物的濃烈氣味,於是我明白為什麽趕馬人身上都有那樣壹種特殊氣味。馬幫規矩,每天吃兩頓飯,早起壹頓,晚上宿營再造飯,白天無論奇書網-整理走多遠妳都得忍著餓。我想別人能忍我當然也能忍,何況腳夫走路,我還騎著馬,問題是我的胃不爭氣,像那些遊手好閑的懶人,吃飽沒事,餓了就鬧意見,而且常常疼出壹身虛汗。我想如果真要遇上險情,比如遭遇野獸,跟土匪搏鬥什麽的,我還有力氣戰鬥嗎?其實這事本來不難解決,提前準備些點心餅幹巧克力,再不濟買幾包方便面,用得著忍饑挨餓嗎?但是馬弄輕蔑地說,偷吃東西(規定時間以外被稱為“偷吃”,奇怪的邏輯!)的人不配做趕馬人,他會被逐出馬幫。
我體會這大概是壹種幫規,相當於軍隊紀律,有人吃東西,有人挨餓,難免影響軍心,所以幹脆大家都不許吃。
下午三點多鐘在壹個地名叫做白花箐的傈僳族寨子外面宿營,我不明白馬幫為什麽早早就休息,得到回答是,馬兒要吃草,所以人就得休息。
這天晚上,我吃到壹頓真正意義上的金三角的野餐。趕馬人在石頭上支起鍋,拾來樹枝生火煮飯。馬弄從馱架上取下壹只鐵筒,打開油布蓋子,掏出壹坨黑糊糊的東西扔在鍋裏。當開水翻滾起來,壹股熟悉的惡臭味直沖腦門,我快樂地嚷起來:“我從前吃過這種東西!”
馬弄驚奇地說:“小漢人(當地人對華人統稱),妳吃過煙籽豆腐?”
我不想告訴他為什麽,自己的事情,不壹定非要別人知道。我等待著,果然不壹會兒湯鍋裏臭味消失,飄出陣陣香味。我迫不及待嘗壹口鮮湯,心快樂地怦怦直跳。我對馬弄說,妳知道為什麽煙籽豆腐美味可口嗎?其實多數植物種子都是油料作物,鴉片煙籽也不例外。用鴉片煙籽腌制食品,早在中國唐代就有記載,宋代稱“禦米”,貴為宮廷食品。蘇東坡詩雲:“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湯就是罌粟籽煎湯。
馬弄嘟噥道:“我才不管妳們漢人怎麽說,我們祖祖輩輩都這樣吃。”
夜裏露宿野地。火堆增加到好幾個,而且都添加圓木,火燃得旺旺的。腳夫取出蓑衣就地鋪下,他們聚在壹起抽煙,我從空氣中漸漸散開來的壹股可疑的香甜氣味中突然意識到,他們是在抽大煙!果然,我看見他們將大煙與生煙絲摻在壹起,然後湊在竹煙筒上輪流抽,這種方法當地稱“舵把筒”。在金三角,抽大煙是件平常事,沒有人大驚小怪。
我還註意到,騾馬被趕到壹起吃草料,貨物堆在火堆中央,這種古老的宿營方式跟錢大宇說的沒有兩樣,只是沒有人值夜班。我心裏忐忑不安,為什麽不安排人站崗呢?萬壹來了野獸怎麽辦?就是偷馬賊牽走幾匹騾馬也是壹大損失啊!但是既然馬弄不安排站崗總有理由,他們是主人,我只好客隨主便。
這壹夜睡得不踏實,山很大,樹很密,營地卻很安靜,只聽見溪水淙淙流淌。我想象老虎黑熊偷偷走近馬群,或者窺視睡覺的人,還有那些專門偷盜馬匹的盜馬賊,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這裏畢竟是金三角叢林,不同於旅遊勝地或者森林公園,壹想到強盜手提大刀嗷嗷直叫的模樣,我就神經緊張。不知白天吃了什麽不幹凈的東西,夜裏起來拉肚子,趕緊吞下幾粒黃連素,下半夜我才昏昏地睡過去。好像剛打個盹,壹睜開眼睛天已經亮了,趕馬人都在收拾馱子,飯也做好了,這說明我昏睡時什麽驚險故事也沒有發生。
我站起身來活動壹下筋骨,在這個大自然懷抱深處,在充滿傳奇色彩的金三角原始森林的馬幫營地,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終於度過平安壹夜,並且準備站起身來去溪水裏漱口洗臉。
這時候我看見壹個不認識的人伸出手,迎面向我走來。
2
關於泰國商人蒙小業先生,我想讀者並不陌生。
蒙小業的父親就是原國民黨師長蒙寶業,母親是孟薩頭人的女兒,與錢大宇母親有遠親關系。錢大宇答應介紹我們認識,但是蒙老板到處奔波做生意,所以壹直沒有機會見面。
蒙小業同錢大宇壹樣,有壹半中國血統,但是他的出生地卻在中國芒市,距離我當知青的隴川縣只有不到壹天的路程,所以他應該自然取得中國國籍。關於他的出生經過本身就是壹部戰爭小說,準確說他還在母親肚子裏就成為俘虜。
我們互相握手,寒暄幾句,原來蒙老板趕了壹夜山路,專程從寮國會曬趕來同馬幫會合。短短幾分鐘,我對這位泰國商人有個初步印象:豪爽、精明、果斷、雷厲風行,不像那些斤斤計較的白臉奸商,倒像個走南闖北的江湖好漢。我想這種氣質大約來自他職業軍人父親的血統遺傳。
蒙小業有壹支手槍,他帶了三個保鏢,每人壹支沖鋒槍,不過都藏在雨衣裏面。我問他這是為什麽?蒙老板答:“在金三角,除了做毒品的走私馬幫,壹般商業馬幫不用擔心搶劫,因為柚木在山裏並不值錢,誰也不值得為這種生意流血。”我說:“妳為什麽要帶槍,妳販毒嗎?”他看我壹眼,笑笑說:“妳這話是犯忌的,我不販毒,但是我不敢說我沒有仇人,金三角任何事都是防不勝防的。”
在這個叫做白花箐的地方,果然到處白花如雲,白花長在大樹上,迎風飄雪。據說這種花可以做菜吃,但是得先放在鍋裏煮,把水倒掉,不然會中毒。當馬幫走在山道上的時候,正是白花開放的季節,風壹刮,花瓣如鵝毛大雪漫天飛舞。腳夫依然埋頭走路,馬兒依然逶迤而行,在這樣壹種花海如潮的壯麗背景下,馬幫的艱苦生活反襯出壹種原始的浪漫情調,但是腳夫個個面無表情,熟視無睹的樣子。我想是艱苦的生活把人變得麻木不仁。不壹會兒我感到渾身不自在起來,脫下衣服壹看,原來皮膚過敏,身上脖子上起了許多紅皰,奇癢難耐。加上夜裏腹瀉未止,腸鳴如鼓,看樣子真是禍不單行。我擔心如果病倒的話,別說采訪,就是馬幫也不能留下來陪妳啊!這是什麽地方?金三角!妳能獨自留在大山裏麽?誰替妳醫病呢?我甚至有些慌張,恨自己不爭氣,偏偏關鍵時候病了,如果考慮周全,應該多備壹些藥,問題是現在後悔沒有用,後悔不能當藥吃。在這個絕望的時候,蒙小業安慰我說:“不要緊,我有萬靈藥水,包妳馬上跟好人壹樣。”
我對他的話將信將疑,什麽萬靈藥水,沒準是什麽巫術之類,要是商人也能治病,豈不人人都成了醫生?我是堅定的唯物論者,從不信邪。蒙小業讓馬弄取來指甲大小壹塊生鴉片,用水溶在碗裏,發出臭烘烘的氣味,看上去跟泥湯差不多。我猛然記起馬鹿塘那位婦女餵咳嗽老者的藥湯,還有那些接生婆向難產婦女灌下的黑色藥水,看來都是這種所謂的萬靈藥水了。蒙小業說:“這是生膏水,妳喝下準會好的。”我堅決搖頭說:“無論什麽神仙水我也不喝。”蒙小業說:“我知道妳不相信它,其實在金三角,生膏水是我們祖祖輩輩治病的良方。妳不試試,怎麽知道沒有用?”
蒙小業最後壹句話起了作用。壹個有勇氣進入金三角的作家是不該拒絕體驗的。六十年代,壹位名叫艾拉的美國女科學家為了進行科學研究,在南美叢林中與黑猩猩共同生活了三十年,這是何等令人肅然起敬的獻身精神!金三角人祖祖輩輩以鴉片水治病,這從壹個側面說明鴉片與當地人生活的重要關系,妳不能親口嘗嘗怎麽知道梨子的滋味?妳的勇氣到哪裏去了呢?
我鼓足勇氣,在眾目睽睽之下把那碗看上去讓人惡心的臟水吞下去,連那些沈澱物也沒有剩下。我絕望地想自己沒準會當場嘔吐,腹疼加劇,吐得上氣不接下氣。沒想到我的腸胃似乎並不排斥生膏水,很快肚子裏有了壹種細雨潤物的很溫暖很熨帖的感受,放出幾個臭屁來,腹瀉居然止住了,人也有了精神。更妙的是,皮膚過敏也不再折磨我,第二天睡覺起來,紅皰完全平復痊愈。
我問蒙小業:“鴉片為什麽有這種奇效?”
他說:“我怎麽知道?反正幾百年來當地人這樣治病總有他們的道理。”
我總結說:“這就有些像中醫,西方人莫名其妙,什麽望聞問切,像搞迷信活動,但是很多醫學奇跡都是中醫創造出來的。”
蒙小業笑笑說:“可能吧。”
我問:“會遇上販毒武裝嗎?比如在這條道上?”
他搖搖頭說:“販毒路線壹般在深山裏,秘密通道,外人不知道,當然不排除他們有時也借商業通道過路。販毒武裝前面有探子,稱‘馬竿’,看上去像采藥人或者打獵的,遇有馬幫,馬竿會發信號給後面,讓他們及時避讓。”
我感到壹絲失望,我說:“聽說這壹帶有坤沙殘部在活動,妳做生意不危險嗎?”
他回答:“危險當然是有的,但是壹般來說金三角有自己的規矩,打個比方,就是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除非政府軍進來打仗。”
我說:“政府軍進來打仗又怎麽樣?”
他說:“那就等於秩序被破壞了,成了壹場混戰。政府軍剿毒,他們分不清誰是毒販,誰是良民,所以幹脆不問青紅皂白,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毒販。當然事實上誰也沒法弄清楚毒販與販毒的區別。”
我驚訝地說:“毒販……與販毒,此話怎講?”
他狡黠壹笑,說:“金三角人人都是良民,但是人人都可能販毒。然而真正的毒販只是少數。”
我說:“比如妳呢?”
他大笑,說:“貧困比毒品更可怕,妳明白嗎?”
我不同意,認為他是詭辯。我反駁說:“妳知道毒品害了多少人?”他回答:“我天天滿世界跑,這點知識我還是有的。”我說:“那麽妳販毒嗎?”他作出驚訝的樣子回答:“我不是做正經柚木生意嗎?”我說:“妳不是說人人都可能販毒嗎?”他想想回答:“我指那些正在販毒的人,因為他們比我窮。”
這天我們在山道上走了壹百多裏路。當晚我們到達國軍老機場所在地孟杯,孟杯是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小鎮,壹條坑窪不平的簡陋街道向我們展示金三角腹地的貧困落後。是夜馬幫按照當地習俗在鎮外宿營,我們則住進鎮上的小旅店。
3
許多年後的蒙小業常常做著這樣壹個夢,他的漢人父親,國民黨師長蒙寶業騎壹匹膘肥體壯的大黑騾子,從金三角的山道上匆匆地奔馳而來。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父親沐浴在殘陽夕照中,春風得意,馬蹄生輝。當然這是壹種意識流,因為那時候泰國商人蒙小業尚未出生,準確說還懷在撣族母親肚子裏,他母親就是前孟薩頭人的女兒籲罕姑娘,漢撣和親的犧牲品。他向我勾畫這幅春風馬蹄圖的時候,我仿佛看見那位籲罕姑娘已經像個風幹的木乃伊。他說那壹天他父親正從壹個遙遠的地方向他走來,他們父子只差壹個月時間就將在這個充滿動蕩不寧的世界上骨肉團聚,然而他父親始終沒能走完這段山路,所以這幅圖畫只好反復出現在兒子的夢境中。
蒙寶業,廣西陸川人,畢業於中央軍校貴州獨山分校,參加過兩次入緬抗戰和反攻滇西戰役,為譚忠老部下,開創金三角的元老之壹。李彌時代,譚忠受排擠,李國輝遭冷遇,蒙寶業自然無所作為。李彌去臺,大權旁落,蒙寶業終於從權力鬥爭的夾縫中出了頭,升任手握大權的第二師上校師長。他指揮的第二師號稱五千人馬,其實也就壹千多人,占據離中緬邊境最近的累班鬧山脈幾個富庶壩子,軍官清壹色為原九十三師老部下,師部駐地三島。蒙寶業大做走私生意,他的地盤正好是金三角主要鴉片產區,所以別人背後送他壹個外號“鴉片師長”。
其實並非蒙寶業偏愛鴉片,用他兒子的話說就是“不得已而為之”。壹個軍人,沒有政治目標,沒有國家利益和奮鬥方向,惟壹緊迫的事情就是養活自己,這不跟土司兵山兵土匪沒有區別嗎?反過來說,在金三角,壹支流亡的軍隊不演變成土匪又能變成什麽呢?
曾經被臺灣報紙譽為反共英雄和熱帶叢林戰專家的國民黨師長蒙寶業,這天騎著壹匹大黑騾子,身後緊跟壹班警衛,個個都騎騾子,挎美式卡賓槍,威風凜凜前呼後擁地穿山過寨,趕回那個地名叫做三島的師部駐地。
三島不是三座島,撣語意為三個漢人官家管轄的地方,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官家,只有蒙寶業是三島的太上皇。蒙寶業滿面紅光,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他的滿足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蒙師長大喜之事有二:壹是老婆籲罕懷胎九月,孫大仙算過命,是個兒子,這是他的頭生兒子。二是他剛剛被蔣介石招到臺灣授勛,國防部長授予他陸軍少將軍銜,從此他就是將軍了。榮升將軍是每個軍人的夢想,盡管授銜的不止他壹人,蔣總統分明也沒有特別記住他,蒙寶業回到江口還是對柳總指揮說了許多感恩戴德的話。其實他心裏很清楚,他所以得此殊榮決非對臺灣做出多麽巨大的貢獻,而是柳總指揮不得不拉攏他。
在江口,柳元麟當頭給他潑了壹盆冷水。
柳元麟說:“第壹敵人肯定要進攻,做好戰鬥準備。第二總部決定收縮防區,三島由第五軍接替,第二師轉移到總部待命。”蒙寶業在心中大罵:媽的×,誰也別想打老子的主意!老子哪裏也不去,敵人來了就跟他們在大山裏打遊擊!如果放棄三島,誰出經費養活老子,誰替老子收大煙糧食!再說與總部挨得那麽近,不定什麽時候姓柳的說變臉就變臉,呂維英甫景雲就是下場!
來到駐地,他先回三島寨子看了太太籲罕,籲罕挺著大肚子迎接丈夫。蒙寶業與其說愛太太,不如說更愛太太肚子裏的兒子,太太已經替他生了兩個女兒,但是沒有兒子就絕了後,這是他的壹塊心病。父親把頭貼近兒子,父子倆隔著壹層薄薄的肚皮交談。兒子聽見父親說:兒啊妳快出來,老子想妳快想瘋了。兒子回答:老爸妳再耐心等等,兒子不會讓妳失望的。
後來父親出了門,沒有去師部而是悄悄來到六團召集軍官秘密開會。他所以避免直接回師部,是因為壹年前柳元麟以臺灣國防部名義向各軍、師派遣特派員,名義上是政治部主任,實際上是安插特務,專幹告密策反的壞事。派給他的政治部主任名字叫邱裏,中校軍官,擅長搞陰謀詭計。這壹招的確很毒辣,等於在他身邊安放了壹顆定時炸彈。只有第三、五軍態度強硬地抵制總部派來的政治軍官,段希文自己任命政治部主任,李文煥跟著效仿,柳元麟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無可奈何。
與會者都是師長的心腹,大家壹致認為不能服從總部的命令。副師長是他的老搭檔,專管鴉片收稅,他算了壹筆賬,如果放棄三島,單單稅收壹項就將損失多少多少,部隊經費只夠維持三個月,往後勢必坐吃山空。而今年大煙長勢格外喜人,到嘴的肥肉怎麽能夠放棄呢?參謀長也在三島娶了當地太太,對總部命令表示不滿,所以與會者達成壹個共識,就是軟磨硬抗,也要找出種種理由拖延時間,反正就是不予執行。壹旦國境對面果然有情況,立即采取兩套作戰方案:利用地形跟敵人周旋,分散上山打遊擊。
傍晚時分,蒙寶業開完秘密會議回師部去,他騎在黑騾子上,心情很是怡然舒暢。他身後跟著壹隊人馬,放眼望去,三島壩子天高地闊,山清水秀,遠近山坡上,燦爛的罌粟花正在怒放,猶如五彩雲霞鋪落人間。壹群飛鳥鳴叫著從頭頂飛過,潮水般的幽香隨風飄來,湧動在半透明的空氣中。剛剛晉升將軍的蒙寶業躊躇滿誌,他抽抽鼻子,覺得花香醉人,連三島的空氣也醉人。他是軍人,不是花前月下的詩人,但是他酷愛罌粟花,這種花香勝過世界上任何最美好的氣味。花香意味著豐收,意味著財源和收入,罌粟是部隊的命根子,也就是他的命根子。金三角,多好啊!天高皇帝遠,猴子稱大王,他是這片土地的主人,沒有人敢於拂逆他的意誌。許多年後蒙小業對我說,他父親的官道註定走不通,因為他眉心有顆短命痣,孫大仙說過那是血光之災,躲不過的。
山道拐個彎,前面壹片小樹林,中間壹株大青樹,華蓋如傘,鶴立雞群。蒙師長看見大樹下拴著壹匹棗紅馬,馬旁站著壹個人,這人穿壹身美式軍服,很悠閑地玩弄壹根鑲銀馬鞭。他心中壹驚,只聽見那人對他笑道:“師長回來了,歡迎歡迎,祝賀榮升將軍……妳們那個會,到底開完了?”
蒙寶業的笑容在臉上凝固了,他認出這人正是臺灣派來的特派員,政治部主任邱裏中校。特派員好像他的影子,無處不在地跟著他,甩都甩不掉。當然他暫時不想與他鬧翻,特派員畢竟是上面的人,來頭很大,因此蒙師長只好裝聾作啞,含糊其詞地企圖蒙混過關。不料特派員上前拉住騾子韁繩說:“請師長對我說明,妳們背著我開了什麽會?否則我立即就向總部匯報。”
如果蒙寶業沒有當上將軍,沒有到臺灣接受蔣介石接見,如果當上將軍的蒙寶業沒有對總部不滿,沒有抗拒命令的念頭,他恐怕就會忍壹忍,小不忍則亂大謀,退壹步天地寬嘛。問題是現在他是將軍了,將軍有自己的尊嚴和脾氣,所以他終於勃然大怒,掏出手槍在特派員頭上重重敲了壹下,警告他說:“妳滾開,我是這裏的長官。聽口令,否則老子槍斃妳——立正!向左轉,開步走!”
鮮血從特派員頭上流下來,蒙寶業騎著騾子得得地走過去,蒙小業聽見他老子在心裏惡狠狠地發誓:“老子造反的話,第壹個就宰了妳!”
4
公元1960年的雨季終於在壹陣緊似壹陣的幹風中漸漸遠去,壹夜之間,擠壓在山頭上的潮濕雲團好像被傳說中那個巫婆的魔袋收走了,山林挺直胸膛,天空變得高遠而明亮。太陽壹露頭,就將那種壓抑已久的澎湃激情轟轟烈烈地釋放出來。湄公河水退下去,沙灘從水中爬出來,撐筏的吆喝聲回蕩在寧靜的河面上。由於地面水分在灼熱的空氣中蒸發,山林終日浮遊著壹層牛乳般的白色霧嵐,好似阿拉伯少女的面紗。泥濘道路變得幹燥而堅硬,果實因成熟而腐爛,種子得以播入泥土。
在這個陽光充足和大地收獲的季節裏,戰爭陰影卻像逼近的沙暴黑雲壹樣壓迫在人們心頭上。戒備森嚴的國民黨江口總部,情報紛至沓來,北方邊境線上,敵人大軍雲集,可以肯定這些敵人的野戰部隊決不是擺在哪裏做做樣子的。西線情報稱,緬軍兵力已經增加到三萬人,三個步兵旅,九個機械化營,沿東枝鐵路渡江東進,準備大舉進攻。
總指揮柳元麟苦著臉研究壹份重要情報,情報稱,北方在邊境劃定壹片“紅線區”,嚴禁作戰部隊越線。
他在這段話下面劃了幾個重重的問號。為什麽要劃出“紅線區”?兵不厭詐,這是不是敵人施放的煙幕彈?壹個以假亂真的花招?西線緬軍並不足懼,就是他們數量再多些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來自北面的老對手。問題是,他們為什麽不直接攻擊江口總部和孟杯機場,與緬軍形成戰略合圍之勢,這樣的話,金三角國民黨的天就塌下來了。他想不通的是,他們為什麽要劃出“紅線區”來縛住自己手腳呢?這不是給對手留出很大的回旋空間嗎?
他問副參謀長錢運周:“妳看這份情報可靠嗎?”
錢運周謹慎回答:“不排除是個迷惑我們的陰謀,需要加以證實。”
總指揮沈吟壹會兒說:“假定這份情報可靠,妳看我們該怎麽辦?”
錢運周更加小心,他知道總指揮是個疑心很重的人,而且獨斷專行,不大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他揣摩長官的意思,對究竟怎樣作戰拿不定主意。他回答說:“假定情報可靠,我建議利用這個紅線區,集中力量重創緬軍,消滅其有生力量,讓仰光政府今後不敢輕舉妄動。如果紅線區是陰謀,我們應該放棄金三角,全面撤退到寮國去,不與敵人正面對抗。”
柳元麟沒有說話,他在作戰地圖前站了許久,然後問:“對緬軍作戰,參謀部有具體計劃嗎?”
錢運周預感到總指揮要下決心打大仗了,他恭恭敬敬回答:“是的,參謀部早就擬定對付緬軍作戰方案,包括與緬軍主力決戰的‘零號方案’。”
柳元麟轉過身來,錢運周看見長官眼睛發亮,這是職業軍人對戰爭的渴望。長官說:“與緬軍主力決戰有把握嗎?”
副參謀長立正回答:“報告長官,‘零號方案’經過反復實地勘察論證,應該有把握實施。”
柳元麟點點頭說:“很好,我們看似被動,其實主動,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且看敵人如何動作。具體說就是且看北面敵人如何動作。”
錢運周說:“我立即派人加強情報收集,嚴密監視國境對面的動靜。是否催促蒙寶業第二師盡快向南撤退或者轉移?”
柳元麟沒有說話,取出壹份電報扔給錢運周,那是第二師政治部主任邱裏密報蒙寶業密謀造反,散布什麽“寧可被共軍消滅,也決不撤離三島”之類蠱惑人心的流言,建議總部火速逮捕第二師軍官,整肅部隊。雲雲。
錢運周覺得背上有冷汗出來。他當然明白蒙寶業不會造反,這個“鴉片師長”是拿三島當命根子,不肯撤出那個富庶的鴉片之鄉。可是告密者這種險惡用心讓人不寒而栗心驚肉跳。柳元麟問他:“妳怎麽看,蒙寶業會不會造反?”
錢運周硬著頭皮回答:“蒙師長是國軍元老,又剛剛被大總統接見,晉升將軍,黨國對他恩重如山,我想他不敢起謀反之心吧。”
柳元麟冷笑道:“莫非邱裏謊報軍情不成?”
錢運周不敢正面回答,他顧左右而言它:“民國三十九年(1950),蒙師長滇南阻敵,與數倍共軍激戰三晝夜,掩護主力安全撤退……”
柳元麟冷笑著打斷他的話:“小錢,妳同我耍花槍啊。我知道妳跟這個蒙寶業是什麽親戚對不對?……實話告訴妳,就是給他六個膽子諒他也不敢造反,他只是要做地頭蛇,保住那塊地盤。我不派去那個邱裏,他不是更加為所欲為了嗎?”
他隨即口授兩道命令:壹道是申斥邱中校僭職越權行為,給予警告處分。另壹道是命令第二師做好阻擊北面敵人的戰鬥準備。
金三角國民黨殘軍像頭狡猾多疑的狐貍,壹面盯著眼前走近的獵物,壹面防備天敵克星的出現,期盼那道“紅線區”奇跡般生效。
5
蒙小業說,那天晚上他父親夢見壹頭大蛇遊來,大蛇頭如小丘,眼如燈籠,只壹吸就把黑騾子吸進肚子裏。父親嚇得兩腿發軟,知道自己遇上蛇精,掏出槍來連連射擊。誰知子彈被那畜生只壹吸,都吸進肚子裏不見了。父親想自己英雄壹世,剛剛晉升將軍,落得如此下場,就傷心地哭起來。誰知這壹哭竟哭醒過來,他連忙把太太叫醒,太太當然也弄不明白這個兆頭是兇是吉,就對他說請孫大仙來占個卦。
關於這位被尊為大仙的孫巫師,我先前並未在意,後來偶然聽人說到孫大仙本名,這才不由得大吃壹驚。原來此人居然不是蠅蠅茍茍的無名鼠輩,而是壹個曾經大名鼎鼎,在中國現代史上曇花壹現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變”壹舉改變中國社會的歷史方向,壹位軍官親手從華清池的假山背後捉住蔣介石,轟動全國,這位壹舉成名天下聞的軍人就是張學良將軍的衛士營長孫銘九。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在南京被扣,東北軍解體,這位孫營長從此銷聲匿跡不知下落。我想蔣介石對這位孫營長壹定印象深刻,所以小人物的消失總是有充足理由的。而當我1998年走進金三角才驚訝地發現,孫銘九居然逃過死神魔爪,輾轉流落到金三角,這真是壹個命運的奇跡。
當地人說,孫大仙專替人算命看相,消災解難,據說看得很準,能預蔔生死未來。有人問他:可知自己生死後事?答曰:死無葬身之地。事實上他的下場果然很悲慘,被人扔下毒蛇洞,印了死無葬身之地的說法。
已經得道成仙的孫銘九端坐在蒲團上,細聽蒙寶業訴說噩夢由來。蒙小業父親年輕時並不信命,吃兵糧的人,只信槍桿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可是隨著成家立業,當上將軍,隊伍多了,家私大了,這才開始信神信命,而且惟恐不夠虔誠。他家中至少供奉了三尊外面請來的各路神仙:如來佛祖,關公大帝,趙公元帥。神仙來路不同,用處也不同,如來領導未來,人難免壹死,到另壹個世界不會下地獄。關公是勇武之神,保佑軍人打勝仗。趙公元帥是財神,只要他老人家高興,就會把錢大把扔進妳的口袋裏。
大仙聽完噩夢,長嘆壹聲說:“不瞞將軍,妳眼前有血光之災呀。”
蒙寶業忙請大仙指點迷津。大仙起身在院子裏打了壹卦,指出禍將北來,不過他已經請動關帝半路顯靈,消弭這股惡煞之氣。蒙寶業大吃壹驚,難道大仙連軍事秘密都能預知?但是孫大仙不肯泄漏天機,只是鄭重指點,十日之內不宜遠行,封閉朝北的門窗,改從南門出入。如不遵循,定有殺身之禍降臨,雲雲。
蒙寶業送走大仙,參謀送來急電,指揮部通報敵情,命令南撤十公裏,情報說第二師將是敵人閃擊的首要目標。蒙寶業放下電報,他看看窗外藍藍的天空,碧綠的大地,陽光亮閃閃地穿過葉縫,像織出道道金線。山坡上罌粟花燦爛開放,再過半月就要開始割大煙,他們為什麽要撤退呢?他忽然覺得敵情通報不真實,敵人還沒有發動進攻,他們有必要驚慌失措嗎?放棄到手的大煙,下半年部隊吃什麽?靠什麽發薪餉?再說孫大仙有言,十日內不宜遠行,於是他發布命令:壹團向北展開警戒,二團向南展開警戒,師部和直屬隊原地不動。
壹連數日平安過去,邊境情報站和警戒哨都沒有發現異常動靜。蒙寶業壹顆懸起的心漸漸放回原處。他遵循大仙囑咐,將屋子門窗壹律改向南開,並在心裏暗暗祈禱,菩薩保佑,只要大煙開割,收完這壹季,躲過這壹災,他蒙寶業壹定給菩薩重塑金身。
這天他照舊在師部值班,騎騾子到處巡視,晚上跟參謀長打牌喝酒,後來突然想起幾天沒有回家,不知老婆肚子裏的兒子怎麽樣,這才囑咐值班軍官,然後頭重腳輕回家去睡覺。原本摸慣房門,不料壹頭撞在墻上,額角上起個包,這才記起房門已經改了方向。
太太籲罕還沒有睡覺,聞見丈夫身上散發的濃重汗味和酒味,知道丈夫又喝多了。撣族女人是男人的奴隸,這壹點很像日本,越是好女人越是好奴隸。太太趕快起身服侍丈夫,直到丈夫在床上打起鼾來。蒙小業說,這個時刻很重要,因為他在母親肚子裏突然聽見槍聲。
槍聲是從寨子外面的師部響起的。震耳的槍聲把整個寨子都驚醒了。蒙寶業壹聽見槍聲就醒過來,他側耳壹聽,沖鋒槍在猛烈射擊。槍聲令他魂飛魄散,敵人果然不聲不響摸進來了,他也顧不上太太和尚未出生的兒子,翻身下床撲向窗口。他的意圖本來很清楚,打算像頭靈巧的山貓或者鹿子縱身壹躍,躥出窗外去,窗外到處都是茂密的灌木叢,因此他就會像魚兒遊進大海壹樣消失。沒想到黑暗中他卻被壹堵冰冷結實的墻壁重重地彈回來,這壹撞是如此沈重,槍也丟掉了,頭也撞暈了,眼冒金星,躺在地下半天起不來,原來他竟忘記自家門窗都改向南邊了。將近四十年前蒙小業與他大腹便便的母親壹道親眼目睹這個悲慘的事實,但是他們顯然都對這個昏頭昏腦陷入困境的笨重男人無能為力。等他終於掙紮爬起來,襲擊者已經闖進家門,雪亮的手電筒光罩住他。
“蒙寶業,妳必須老老實實……優待俘虜,否則自取滅亡!”襲擊者用清楚的漢語警告說。蒙寶業停止反抗,他對這種警告方式真是再熟悉不過,誰要是受到警告,說明妳已經被死神咬住喉嚨。他乖乖站身起來,像嬰兒那樣無助而可憐地看了女人壹眼,太太嚇得只會哭泣,肚子裏的兒子跟著母親壹起顫抖。這個父親謙卑地對襲擊者懇求:“請千萬不要傷害……女人,她快要生孩子了。”
可以想象,這天夜裏三島變成壹座煉鋼爐,寨子裏到處鋼花飛濺,到處都在起火,都在熊熊燃燒。蒙寶業被押著往外走,同蒙寶業壹道走出寨子的還有女人和女人肚子裏的兒子。兒子認為父親壹定後悔得想自殺,十天不出門就等於自取滅亡,但是誰叫妳相信巫師的壹派胡言呢?而他那些混賬部下,竟然連壹個警報都沒有發出來就讓師長做了俘虜。
總之從這天起三島的天就塌下來,蒙寶業和他的家庭以及這支番號為國民黨第二師的部隊陷入沒頂之災。當俘虜押出寨子,踏上山道,彌漫在金三角土地上的罌粟花正在熱烈開放,花香還是那麽濃烈,空氣還是那麽醉人,這對蒙小業的軍人父親來說好像是種大膽鼓勵,是種深情挽留。蒙太太最後看到丈夫是在壹座山崖邊,丈夫突然像豹子那樣躥起來,壹連撞倒幾個人,然後滾下路邊深谷。這是充滿絕望和瘋狂的反抗,因為俘虜手臂被捆綁著,基本上沒有成功逃跑的可能。蒙小業說,當槍聲猛烈地響起來,母親壹下子就癱倒在地上,這個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男人從此被黑暗吞沒,從他們的生活中永遠消失……
6
壹夜之間,對手神話般出現,鐵錘砸在蒙寶業第二師頭上。柳元麟緊急下令各部隊放棄陣地,脫離紅線區靜觀戰局發展。
此後數日,第壹、二軍均與之接觸,交火後快速後撤。
在壹片近於窒息的等待和心跳中,奇跡果然發生,代表敵人的紅色小旗果然停留在紅線邊緣上,不再越雷池壹步。幾乎同時,西線情報飛來,大批緬兵渡過薩爾溫江,在飛機掩護下沿景(棟)大(其力)公路向東推進,已經與三、五軍前哨接上火。
決戰開始了。